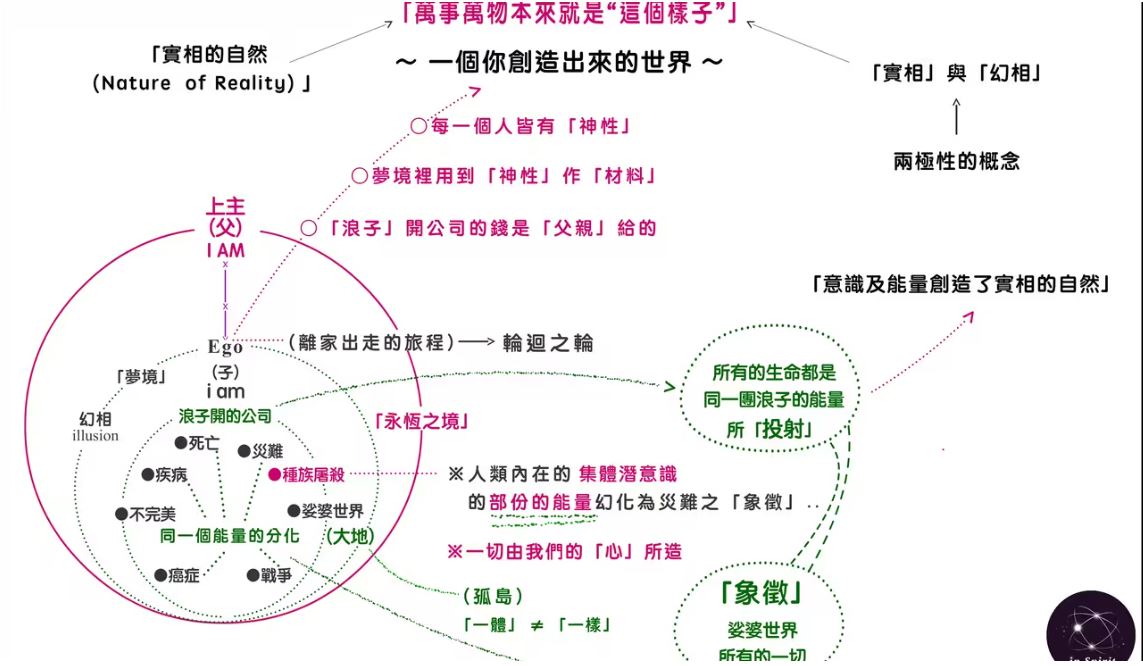賽斯-未知的實相一
夏日即冬日
今日即明日,而現在即過去,
萬事皆空而事事皆恆久。
既無開始,也無結朿,
既無可墮落之深,也無可攀升之高。
只有這一剎那,這光之搖曳,
遍照空無,但哦!如此光明!
因我們即在太空顫動不定的火花,
燃盡永恆於一剎之恩寵。
因為今日即明日,而現在即過去。
萬事皆空而事事皆恆久。
(羅的註:這是一九六三年四月,當珍二十三歲時寫的一首詩的第二及最後一節。縱使在這不成熟的作品裡,她的神秘天性已在肯定其與生俱有的知識。)
羅的前言
賽斯在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的第六七九節開始口授《“未知的”實相:賽斯書》,而在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的第七四四節完成。
賽斯如往常一樣一節節的口授此書,但卻取消了任何章節的形式。不過他的確把他的資料組合成六段,並且加上標題。如他在第七四三節裡吿訴我們:“這本書沒有章節,為的是更進一步的瓦解掉你們對一本書應該是怎麽樣的概念。不過,仍然有不同類的組織存在着,而且本書的任何一段都同時要求讀者好幾個層面的意識之參與。”賽斯並沒有給每一節一個標題,因此在目錄所列的每一節之後珍打算寫上幾句話,至少指出在那節裡所論及的一些主題。
就像其他的賽斯書一樣,《“未知的”實相》不只包涵了賽斯課,也還有珍和我對它們的想法,以及我們有關其製作環境的註記。
我很好奇想要知道,珍實際上花在製作這整本書上的時間大致有多少,經我計算的結果,她在九十點三五個小時的出神時間裡完成了這本書,再加上休息時間總共是一百三十一點三96個小時。我覺得蠻迷惑的,為什麽以前幾乎每一個讀者都忽略了珍製作賽斯書的速度,甚至珍本人對此也沒有表示過多少好奇心。但我認為她的製作速度是對賽斯的概念——基本上一切都同時存在的一個最佳解釋:時間並不存在,而賽斯書已經以完成了的形式等在那兒。
我認為偶爾在本書中提醒讀者賽斯的某些基本概念是很重要的,舉例來說,我會繼續談到時間——但卻是賽斯的時間——的問題,把它和賽斯所說的一種“耐久性”(durability)一同來談,這種耐久性同時是“自發性”及“同時性”的,如賽斯不只一次解釋給我們聽的。這個“耐久性”是透過“價值完成”之不斷擴展而達成的。我在卷二的第七二四節之後的部分評論也適用於此:“如賽斯在一九**年一月八日的第十四節中相當幽默地說:‘……你們拫本不知道對一個必須花時間去瞭解的人解釋時間有多麽難。’然而,賽斯的‘同時性’時間並非絶對的,因為就如他在那節裡也吿訴我們的:‘雖然我不受你們層面的時間所影響,我卻受在我的層面上某些類似時間的東西所影響……對我而言,時間可以被操縱,可以悠閒的去用及檢視。對我而言,你們的時間是一種工具,是我可以用來進入你們的覺察的幾個途經之一。因此,它對我仍然是某一種的實相。否則的話,我就根本無法以任何方式利用它。’
我想,只要我們是具體的生物,就永遠無法抓住賽斯“同時性時間”的觀念,然而,它卻對無形的機制提供了線索——我們就能比較瞭解珍眼中的賽斯。把概念變成文字這件事(盡珍所能做到的),有助於讓我們抓住賽斯所講的:我們可以對時間做出某種直覺性的、非語言性的觸及或了悟,那多少超越了我們對所謂“時間”的素質或本質之陳腐概念,這陳腐概念在我們西方社會是如此的理所當然,以致於甚至去質疑其彷彿單方向的流動也是徒然的。
下面我要引用賽斯的兩段話,然後再繼之以珍的一段較長的話。
賽斯的第一段摘錄是為了在兩卷《“未知的”實相》之間創造一個橋樑,藉由自其中一卷提出一些東西而將之放在另一卷裡。再次的,由卷二的第七四三節:“沒有一本名為《“未知的”實相》的書可以使得那個實相完全被認識。它仍然是星雲似的渾噸,因為它在意識上並未被了悟。我所能做的只不過是指出那些比較看不見的區域,幫助你們探索你們自己意識的不同面……我十分明白這本書引起的問題比它回答的更多,而那原是我的意圖……”
如我在某些注裡引用的,珍早年的詩淸楚的反映出,她對某些賽斯日後詳細闡釋的觀念之直覺性瞭解。就我看來,她對賽斯資料所負的任務就是提供這些基本上藝術性的概唸給我們有意識的運用,以使它們在我們日常生活裡的運用將我們個人與集體的實相變得更好;而我所謂的“藝術性的概念”是指人類所能表達並且爭論的,最深、最美而且實際——並且,沒錯,神秘——的真理與問題。
在賽斯書裡我們一直故意避免去評論存在於賽斯的觀念及那些近東、中東或遠東的種種96宗敎的、哲學的及神秘的理論之間的類似性。當然,這種方式適合我們的本性,珍和我知道此種關連性存在——的確,如果它們不存在我們才會覺得奇怪呢!別人常常跟我們談到這一點,而我們也讀了一些,好比說,談佛教、印度教、禪與道家的東西,更別說像印第安巫術、巫毒及西印度群島的巫術了。我們認為,顯然可以寫一本書來比較賽斯資料與其他的思想體系——不論它們是否是宗教性的,但因為珍和我都是個人主義者,所以選擇了不去集中在那些區域。而我在此所說的也不是想要眨低其他對“基本的”實相之看法。
那麽,雖然在賽斯的哲學及許多其他有組織的思想系統之間是有相似處,但在我們看來也有重大的不同。珍和我傾向於認為,我們在我們世界裡發現的那種一致性“涵括”了宗敎,而非被它們界定,而我們認為賽斯也強調此點。我們就這樣頑固的向前走,明白我們的觀點是根植於世界的西方傳統裡,但也知道在我們四周存在着許許多多其他的哲學或體系,它們之中有些已存在數世紀之久,那是人類創造出來解釋實相的。然而,我們並不覺得我們非得深入瞭解,好比說,蘇菲教或婆羅門教之細節不可。但我們不喜歡印度教與佛教的涅槃概念,它們主張通常在一連串的生命之後個人意識之滅絶,並溶入於一無上的神靈。而且我們反對那種說法:“大自然”以線性時間的方式做了這樣的安排,使得個人必須在此生中對前生的行為償還因果的債。如果大自然不處罰任何事,為什麽要處罰任何人?涅槃和業報的實相併不是珍和我想要創造的。
反之,我們比較喜歡賽斯的——是我們自己的觀念,關於個人意識之不可侵犯,不論在肉體存在之前、之中或之後,也不論是涉及了任何一種的轉世理論。也許對我們這些活在西方的人而言,我們自然不會喜歡在肉體死亡時捨棄我們的個人性這種概念,即使在理性上我們能瞭解,比如說,佛教的教義說我們能在最終的、至樂的捨棄自身於一無上神靈裡找到“完美的”喜悅——雖然我幽默的說,就我個人而言,我還不知道那個捨棄自己的人怎麽知道他這樣做了沒有,如果他已被如此徹底的溶入了的話。
我比較同意賽斯在《靈魂永生》第二十二章第五九〇節裡吿訴我們的:“你們不是命定要溶入於‘一切萬有’。如你目前所瞭解的你人格的形貌將會被保留。‘一切萬有’是個人性的創造者,而非毀滅它的手段。”而每當我讀到傳統東方對無上神靈的觀念時,我就記起賽斯在《靈魂永生》附錄裡第五九六節說的:“在此,我用了‘意識的擴展’這個詞,而非更常用的‘宇宙意識’,因為後者暗示了在此時人類尚不可得的那種比例之經驗,與你們正常狀態對比之下,強烈的意識擴展在本質上也許顯得是宇宙性的,但它們僅只是對你們現在就可得到的意識之可能性的一個暗示而已,更別說能開始接近一個真正的宇宙性知覺了。”
我假定上面那四段話很顯然可能引起許多非議,但在其中的資料很接近於珍和我在這些96日子裡對賽斯資料與其他哲學之關連性的看法。我尤其覺得高興的是,珍的工作及她對我們思想的貢獻是出自她的心靈,而未得助於實驗室、統計數字或測驗。那就是說,我們對真正考驗的想法是在觀察,以看出賽斯資料能對實際的日常生活有何幫助。我們在一九六五到六六年做的,其他種類更“正式”的測驗,詳細的紀錄在《靈界的訊息》第八章裡;我們現在很容易忘記那些早期的測驗是相當的成功,而且可以在任何時候再來一次。當我們在做那些測驗時,我心裡覺得奇怪為什麽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當中,只有人類這種動物覺得有需要去建造實驗室來“證實”他到底是什麽,他的能力——心電感應、新陳代謝或其他——又到底是什麽。這個題目本身就如此的龐大,以致於珍和我可以一直寫個不完,因此,我只在這兒約略提及一下。
根據他認為他已知的東西,在他的實驗裡因此有很大的機會去獲得預先設定的答案:他的外在化的設備幾乎無法產生其他的結果。(一個科學家不稱一個氧原子或任何一個其他元素為活的,更別說它們是具有意識的了。然而,某些原子聚合成的一個人形卻稱他自己是活的——而激烈的否定那些不倖存在於人類架構之外的一模一樣的原子群同樣的地位。)但在賽斯過去十年裡所給的資料之中,他討論過人們對一般人類狀況之極度貧乏的瞭解的某些理由,而我也確信將來還會談得更多。
我覺得極為欣慰,珍只用到她現有有形的身體及無形的心智就能持續地顯示出人類不被認為具有的能力,我們不滿意我們的社會——不論東方或西方——給我們的答案。對如生命的意義,其深度與神秘,其無窮盡的可能性這類問題,每個讀者可以在賽斯的看法裡找到他自己的意義。
以下是錄自賽斯的第七五〇節,那是在他完成了卷二的兩個月之後,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舉行的,在其中他不只簡略的說出製作《“未知的”實相》的動機,並且還論及他的一個我認為應該經常強調的基本概念,這一次還涉及了知覺。“《“未知的”實相》寫來是要給……個人對實相的其他模式略見一瞥。它是要被用來作為一張地圖,把人領入並非另一個客觀的宇宙,而是進入意識的內在道路。這些內在道路或意識股(strands)帶進來一些要素,使得人變得可能去瞭解,任何一個客觀化的宇宙之內涵真的可以被十分不同地知覺到。你就是你所知覺的東西之一部分,當你改變你知覺的焦點時,你便自動地改變了客觀的世界。並不只是當你知覺它為不同的東西時,它卻還保持原狀,而不論你的經驗為何。知覺這個行為本身有助於形成被知覺之事,並且是其一部分。”
以下是珍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寫下她作為賽斯的觀感之摘錄:
“當我是賽斯時,我只是他的實相之一小部分,也許只是我能捉住的那個部分,但96我卻沐浴在那個人化的能量裡。當賽斯把注意力轉向人們,對他們說話或回答問題,那時我感覺到對他們的價值及個人性的一種幾乎是多次元的欣賞。他瞭解每一個人的價值並向其致敬,以一種與我們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人。我對賽斯對別人的反應的那種體驗,使得我懷疑有一種比我們所知遠較生動的情感經驗存在。
“然而,我確知賽斯代表了另外一種朿西,一種不同的人性,而當那種樣的生靈與我的主觀世界相交時,賽斯就‘發生了’。
“在許多方面我們是一種孤獨的種族。我們彷彿永遠梭巡於我們自己的天性之藩籬內。也許我們對身份感的概念是有如我們繞着我們心智畫的一個神奇的圈子,使得任何在外的東西顯得是黑暗又陌異而‘非我’的。也許有遠比我們自己亮得多的其他心靈之火照亮那內在的景觀;還有意識的其他面,我們與之相連,就如我們與動物相連一樣,在一種我們幾乎不瞭解的存在之鏈裡。
“我們愛‘向後’看我們的動物本源,我們設定所謂的進化已經結束,而我們在此歡呼——哈哈,我是萬物之靈。但也許我們只是在中間,不完全的感覺到我們自己之其他遙遠版本的存在,那將出現在一個遠得我們無法理解的‘未來’。也許以那種說法,我是賽斯的某個遠祖,活在我自己的生命裡,卻只是他生命裡的一個記憶。但他堅持在過96去裡也有新鮮的行動;所以如果事實是那樣的話,我就仍在尋找我自己的途徑。
“當我自己想到這麽遠的時候,一種奇特的加速攫住了我。我的身體變得非常鬆弛,但我的心智卻有一種很奇怪的運動感,就好像我試圖去瞭解的某些東西太快的掠過我,而令我無法追隨;然而,我一直試着使自己旋轉得更快些,以便追上去。如果我的一個細胞想要理解我自已的主觀實相,它也許會有同樣的感覺。我想我是活在賽斯的主觀‘身體’內,就像我的一個細胞是活在我的肉體內一樣。只不過,我一直在摸索……並且感覺那些我自己的實相併不能真的瞭解的事件。
“這也許只是當意識心試圖瞥見它自己源頭時的反應而已。也許當我們在做這種嘗試時,象徵性地說,就好比我們是暫棲在我們意識的平台上,同時向上也向下看。就像無重量的太空人,我們知道我們是誰,卻不太確定我們的位置,因為心理上它在內在空間裡不斷的改變。我們暫時的暈眩了,被一個自己與自己的其他版本所組成的內在宇宙弄得眼花撩亂,而感覺我們正旅遊過某種龐大的心靈,它播種‘自己’就如太空播種星辰一樣。”
最後,我們如何應付越來越多的讀者來信呢?我們最近的作法是寄給讀者三樣東西,一封珍和我的短箋,一封賽斯在一九七五年四月裡口授的信,及一張珍的書單。
96以前賽斯也會口授過一封信,讀者可以在《個人實相的本質》第八章的第六三三節裡找到。我們感覺賽斯這兩封信反映出他資料的大半精髓,以及製作那些資料時我們的境況與心態。我們的確認為把賽斯的新信放在這裡是一個結束這些注的理想方式(信中一如往常賽斯稱珍為魯柏,稱我為約瑟)。
親愛的讀者:
魯柏看過你的信了,約瑟也一樣,我對其內容也是知道的。我們還沒有任何外在的組織,因而沒有秘書可以幫忙回信,也沒有中間人去寫花俏而預先包裝好的回信。
魯柏及約瑟是注重個人隱私的人。他們與宇宙也有種一對一的關係,這種特質是指他們抗拒形成任何組織,即使這種組織會有助於回信。所以我來口授這封信。雖然它會被寄給你們當中的許多人,但它卻是寫給你們每一個人的,而我只是覺得遺憾,我無法個別的深入於你們的熱望、挑戰與問題裡。
你們有些人在喜悅中寫信來,有些則在憂傷中寫信來;你們有些人寫信來訴說你們已找到的答案,而有些人則寫信來要求答案。在任何情形裡,能量都隨著這封信送出去給你們了。
那能量會喚起你們自己的能力,它會引你們到只有自己能有的洞見與解決之道,它會讓你們與自己存在的基礎接觸,而終究來說,所有的狂喜與答案都是由之湧現的。我的目的並非為你解決問題,卻是令你與你自己的力量接觸,我的目的並不是要藉由給你即使是最悲慘問題之“答案”而介入於你與你自己的自由之間。我的目的是要加強你自己的力量,因為終究來講,你存在的神奇就足以幫助你找到成就、瞭解、豐富與平靜。
你們的問題是被自己的懷疑所引起的,這些懷疑的升起是因為你們已與自己存在的價值失去了聯繫。讓我在此加強那個價值,讓我加強我對你們天生具有歡喜隨緣而超脫任何你們現有問題之能力的信心。如果我逕自去替你們解決問題的話,那麽我就否定了你們自己的力量,而更進一步的加強了你們已有的無力感。不過,我知道你們可能會覺得累了,而有時候送你們一份能量可以令你們振奮一下,所以再說一次,隨著這封信我送給你我對你的存在之歡喜的認可——以及你可以用來加強你自己的活力與力量的能量。
並非所有的信都是由郵差送達的,因此就你們所寄給我的信而言,你們每個人應該都有來自我的你們自己那種內在的回應。不過,我在許多方面是作為你們自己心靈的一96個發言人,所以那內在的訊息會是來自你自己更大的存在;由那個多次元的實相層面我向你致敬。
你和“未知的”實相(一)
賽斯序
(珍在出神狀態中傳述賽斯序的情況記錄在第一部,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的第六八五節裡,在那節的中場休息時,賽斯在十點五十七分開始講下面的資料。)
現在:序:有一個“未知的”實相,我是其一部分,而你們也一樣。
(停頓良久。)許久以前,我突然出現在你們的時空裡,自那時起,我跟許多人談過話,而這是我的第三本書,如果我是以一般的方式藉由肉體誕生在你們世界裡的話,這一切對任何人而言就沒有什麽好奇怪的了,反之,我卻開始透過珍﹒羅伯茲說話,以表達我自己。在所有這一切當中都有一個目的,而那個目的的一部分就孕涵在現在這本書裡。
每個個人都是未知的實相之一部分。可是,由於我的地位,我顯然比大多數人更是其一部分,我在心理上的覺知聯繫了你們有意識地覺知的世界及其他至少彷彿逃過了你們注意的世界。我透過她說話的那個女人發現她處於一種不尋常的狀況,因為沒有任何理論——形上的、心理的或其他——可以適當的解釋她的經驗。所以這使得她去發展她自己的理論,而這本書是某些已在《意識的探險》(注一)裡提過概念的一個延伸。為了寫那本書,魯柏汲取了能量的深源。
(十一點十一分。)可是,以你們的話來說,這未知的實相是未知到超過了最具彈性的意識所能企及的,而它只能被像我這樣一個潛伏在其中的人格所趨近。不過,一旦被表達之後,它就能被理解。那麽,我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這未知的實相為你們有意識的知曉。
從歷史上來看,人一度認為只有一個世界。現在他知道並非如此了,但他仍執著於一個神,一個自己,及藉以表達這自己的一個身體的這些概念。
只有一個神,但在祂之內有許多個神;只有一個自己,但在他之內有許多個自己。在一個時間裡只有一個身體,但自己在其他的時間裡有其他的身體。所有的“時間”都同時存在。
(停頓良久。)以歷史性的說法,人類選擇了某一條發展的路線。在其中,他的意識專門化了,集中焦點在極為特殊的經驗上。但心理上及生理上來說,永遠與生具有改變那個模式的可能性,一種會有效的把人類提升到另一種氣候的改變。
(十一點二十二分。)不過,這樣的一種發展首先需要寬廣化對自己的概念,並且對人類潛能有更大的瞭解。人類意識現在正在一個階段,在其間,這種發展不只是可行的,並且是必要的,如果人類想要達成他最大成就的話。
到某個程度,珍﹒羅伯茲的經驗暗示了人類心靈的多次元本質,並且給予潛藏在每個個96人內的能力之線索。這些都是你們種族傳承的一部分,它們顯示出那連接你們居於其中的已知與“未知”的實相之心靈橋樑。
只要你們對自己的本質仍然持有非常侷限性的觀念,你們就無法開始理解一個多次元的神性或一個宇宙性實相,在其中所有的意識都獨特而不可侵犯,卻又熱衷於形成具有組織及意義的無窮盡之完形(gestalts)。
在我其他的書裡,我用了許多已被接受的概唸作為跳板,來把讀者帶到其他的瞭解層面。在這兒我想說明的是,這本書將開創一個旅程,在其中可能看起來熟悉的東西已被遠遠的留在後面了。但是當我結束時,我希望你們會發現那已知的實相甚至變得更可貴、更“真實”,因為你會發現它被一個“未知的”實相之豐富組織內外徹照,並看見那“未知的”實相在日常生活最親密的部分浮現出來。請等我們一會兒。(在十一點三十五分停頓。)個人地及群體地,你對個人性的觀念限制了你,然而,你們的宗教、形上學、歷史,甚或你們的科學都依你們對你是誰或是什麽的概念而定。你們的心理學並沒有解釋你們自己的實相,它們無法涵蓋你們的經驗。你們的宗教並沒能解釋你們更大的實相,而你們的科學也讓你們對你們居於其中的宇宙之本質同樣的無知。
這些組織與學問是由個人所組成的,而每一個都被對他們自己的私人實相之侷限性概念所限制:所以,我們將以個人實相來開始,而且也永遠會回到它上面。這本書裡的這些概念是想要擴展每個讀者的私人實相。它們也許看起來很神秘或複雜,但任何一個決心想瞭解自己及其更大世界之未知因素的本質的人,都有能力企及。
因此,這本書有一個私人性的開始。珍﹒羅伯茲的先生羅勃﹒柏茲對他母親的死(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想要有更多的瞭解。在一節課裡(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第六七九節)他拿出一些舊照片。現在:死後生活之描述通常與眾所接受的一個自己(oneself)的老概念及個人性(personhood)的侷限性觀念一致。不過,我卻利用那個機會來開始這一本書。
(停頓良久。)當“自己”活在肉體中時,它是多次元的。它是靈性與心理性本體的勝利,不斷由無數的可能實相中選擇它自己清晰而堅定不移的焦點(非常熱切的)。當你沒認識此點時,你就會把所有老的誤解投射到死後的生活上。你預期死者與生者沒多少不同——如果你真相信來世的話——但也許更平靜些、更明白些,並且,如果運氣好的話,更睿智些。
(在十一點五十一分停頓——然後非常強調的說:)事實是,在人生裡,你很巧妙卻又完美地懸在實相之間,而在死後你也一樣。於是,我利用那機會來解釋羅的母親在死後所能得的大幅度自由——但也解釋在她生時就在的她實相的那些成分,那在意識上對她而言是關閉的——由於人類對心靈本質的觀念之故。我偶爾評論那些屬於柏茲家庭〔包括珍〕的照片,但任何讀者都可以看看自己的老照片而問同樣的問題,把在此地所說的應用到私人經驗上。“未知的”實相——你是它的已知的同等物(再次更大聲的)。那麽,認識你自己,當你變得熟悉這些概念時,你的意識會擴展。我自己則代表你的存在之那些已然了悟的部分。我的聲音自你也在其中享有經驗的心靈階層升起,所以,傾聽你自己的“知曉”吧。
(快活的:)序言結束。
(十二點〇一分。)
注一:事實上這個月初(一九七四年二月)珍開始她《意識的探險:層面心理學入門》之最後完稿。不過,她已把她在裡面所談所有主題之細節整理好了。
譯 序
王季慶
《“未知的”實相》是賽斯書中最厚又最難譯的一本,原書兩卷共有八百頁之多,實在令人望之卻步!但若存而不譯,賽斯系列不但不完整,而且也漏失了許多精義。所以,在一九九三年春節期間,我和許添盛便放了串鞭炮慶祝“開工”了。
這本書的好處在賽斯和羅的序中已可見一斑。我自己則源源為其對“可能性”之討論所震撼!這種“可能性”瀰漫於所有的時間、空間,也就是,當你出於自由意志而選擇了某一條路線時,那未被選擇的可能性則會在另一個實相裡,由你可能的自己去經驗。這個理論可以說是匪夷所思,若去追究其“暗示”,會令人頭殻發脹,並且興起“無常”之感!
但在我譯的另一本書《超越量子》裡,物理學卻已印證這了這種“大千世界”的理論,證明賽斯所說“每一個可能性都會被實現”的確是“可能的”!
而我們當下的每一剎那,並非受限於線性時間的過去與未來,卻是由我們最深的源頭冒出來的,是憋在過去與未來之間的一個“可能”。所以這種“非命定”和“無常”,不但不應令你恐慌或茫然,反而提供了你把握“當下”的理由,並且鼓勵隨機的創造性,因為你的人生“當下”就可被你改變!
以下是特別發人深省的幾段,願先引在此以饗讀者:
·在細胞內的意識知道它自己的不可摧毀性,只改變了形式……雖然細胞實質的死去,但其不可侵犯的本質卻未被出賣,它只不過不再是物質性的。
·所有的生命都是合作性的,而所有的生命都知道它的存在是超越其形體的。
·人這種意識強烈的與身體認同是必要的,以便把焦點集中於具體的操縱。
·所有自然的東西都有“精靈”……它們的確有一個能量的實相,而它們幫助把能量轉換成物質形式……你感覺到風及其效應,但你卻無法看到風,風本身是看不見的。因而這些其他的力量也是看不見的。……它們並不比風更善或更惡……因為你們通常想像,如果某些東西是善的,那麽必然有一個相對的惡的力量,但並非如此……以更大的說法,這些力量是善的,它們是保護性的,它們滋養每一樣活的東西。
·沒有瞭解或訓練,你就必須“失去”你自己的意識才能覺知“其他”意識。
·“你的藍圖”之資料被織入基因與染色體,但卻與之“分開地”存在。
羅記錄了珍傳述此書的時間,才不到一百小時。但我粗略估計我口譯的速度,平均一小時一頁。也就是說,我和許添盛埋頭努力了八百小時才竟全功!(當然,原書還需算上羅寫注和附錄等所花的時間。)無論如何,在一九九四年春節前,我們完成了此書,整整一年的苦功!希望讀者耐心、細心的看完,也與我們一樣,同感這是值得的!
特別要感謝陳建志費心校訂此書,並提供寶貴的意見。
第一部:你和“未知的”實相
第六七九節 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 星期一 晚上九點四十一分
(在課開始之前,我給珍看一張她童年的照片,還有一張我的。這兩張照片差不多同樣尺寸,大約3.25×5寸,都相似的褪色易脆——好像是在同一個時候拍下來的——雖然我那張比珍的要老上二十年。
(我那張照片是我父親拍的,並且記下了日期,已經在我們的家庭相簿裡放了五十三年了。那張照片是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照的,那時我差不多快兩歲,有一頭捲曲的淺色頭髮,穿著小西裝、白色長襪及黑皮鞋,站在位於賓州東北的一個叫曼斯菲爾的小大學城,我父母租的房子的邊院裡。大約有一打小雞聚在我腳邊的草地上,而我頗入迷的向下看著它們。在我身後有個焦點模糊、不知名的十來歲女孩,坐在由樹榦上懸下的鞦韆上,而在她旁邊有一個空的藤編嬰兒推車〔我的嗎?〕,在她後面的私人車道上停有一部有蓬頂的四門汽車。曼斯菲爾離珍和我現在住的紐約州艾爾默拉城只有三十五哩。
(珍的照片已有三十三年之久了,那是由一位較年長的女士替她拍的,她招待珍到紐約州的度假聖地撒拉托加溫泉市市外的一個溫泉區去玩。那時珍與她卧病的母親瑪麗及一位幫96佣住在那個市裡。珍把她朋友的名字及日期以幼稚的字跡寫在照片背後。許多年之後她告訴我:“我媽媽恨那個女人。”在那張快照裡,那是在一九四一年八月的一個陽光普照的日子,珍那時是十二歲,她坐在草地上,後面有一些長綠灌木,她用右手撐地身子略為後傾,兩隻光腿頗為一本正經的交疊。她穿著一件特洛伊市天主教孤兒院送她的印花布衣裳,那個孤兒院離她家有三十五英哩,在此之前她曾在那兒待過十八個月,那時她的母親正在另一個城裡住院治療風濕性關節炎。珍還穿著一件短袖套頭毛衣,那是她母親在住院時織的。
(珍的金髮——後來變得頗黑了——整整齊齊的中分梳理,上頭還夾着一個髮夾。她有着一張年輕的圓臉,但卻面無笑容,她並沒皺眉,而只是直視着照相者,顯出一種嚴肅而幾乎不合她年齡的自製表情……
(對我而言,兩張照片都有我覺得引人好奇的某種神秘感——一種氣氛,我猜部分是由於他們是老舊的、私人的、且是如此的不可取代,但長久以來我都覺察到有些與之相連的其他感覺。珍在一九六三年尾開始傳述賽斯資料,而很快的賽斯就開始發展他可能性的概念(注一)。從此有許多次,當我看著這些快照時,我會發現自己在臆測環繞着那兩個小孩的可能實相。現在我告訴珍,我瞭解我們每個人選擇了那些要使它具體化——或以我們的話來說“真實”——的行動路線。但自從那些照片拍下來之後,我們可能的自己踏上的所有其他路線又96是什麽呢?到如今,那些照片是否真的描繪我們不成熟的身影,我們認為並且一直就是的珍和羅?或從我們的觀點,它們顯示了一個可能的珍,一個可能的羅——兩個早已走上他們自己的旅程到其他的實相裡去了?我不太清楚我想知道什麽,也很難向珍表明我的意思。也許我只是想要賽斯以一種更個人的方式談談可能性〔後加的:在那時我完全沒想到我的問題會引發一本新的賽斯書〕。
(珍在出神狀態變為賽斯的外在跡象其本身就非常有趣,而我不想加以忽略;的確,我常常描述它們。不過,真令我着迷的是她在課中所表現的我所謂大大加強了的意識或能量——而我總是在她的傳述表面之下感覺到一股甚至更有力的能量之流。當珍安靜的坐在她的甘迺迪搖椅裡等待賽斯過來時,我這樣想著。幾分鐘後,她的右手伸向她的眼鏡,當她把眼鏡拿下來時,她的眼睛比平時黑亮得多:她已在出神狀態了,賽斯已在那兒瞪着我了。)
現在:晚安。
(“賽斯晚安。”)
(身為賽斯,珍翻看了一下我放在我們之間咖啡桌上的照片。)
我現在要談這兩張照片——但如果你想要的話,你也可以有關於任何一張照片的資料。
(“好的。”)
再說一次,你們每個人選擇你們自己的父母及環境。你在兩天以前的筆記裡談到與藝術有關的預知,以那種說法,預知也適用於你的出生,你在事前在無意識層面上已十分覺知你會碰到的那些情況,你選擇了它們,並且事先把它們投射進入時間的媒介裡。
不過,那些情況雖然在一種方式裡被“設定”了,但在另一種方式卻是非常具可塑性的,因此,各式各樣的可能事件能自它們流出。預知性地說,你對任何一個行為或路線之結果在無意識上都十分的覺察。當魯柏(注二)這張照片被拍下時,他已開始變得覺察到那些會主宰他未來生活的他全盤興趣之所在,雖然其特定路線尚未被選擇。
這些興趣之中有一些對魯柏目前的經驗提供了一些解釋。那時宗教的背景就已在了。由於他的偏好與要求,在三年級之後他從一所公立學校轉到天主教學校(注三),這件事是他母親所不贊同的,他母親覺得公立學校比較好,對人際關係也較有幫助。魯柏在那個年齡就相當有主見了,他強迫他母親答應他換學校。他製造出如此的紛擾,大哭大鬧以致於他母親不得不答應。他甚至在那時就已很頑固了。
他一直是極有想像力的,他母親也是一樣。他母親有點反叛社會,與社會上“不體面”的分子在一起以炫耀她的美貌。在很久以後,魯柏也與他環境裡“不體面”的男人約會,但母親或女兒都沒有見到彼此的那個相似性。到那時,魯柏的母親要魯柏有一個可尊敬的、最好還頗富有的丈夫,而無法瞭解他為什麽選擇那些不肯隨俗的人。
魯柏選擇了一個貧窮的背景,就像他的母親一樣。那母親也很聰明,但為逃避(她的環境)之故,選擇了依靠她的美貌。魯柏則試着用他的頭腦。那些資料(多年來在一連串的私人課裡)已給過了。
(“是的。”)
魯柏則以非傳統概念之更大的架構來表現他的不隨流俗。在其背後,作為一個受福利部組織救濟之下的孩子,縱容自己、小小的奢侈或太不隨俗的行為在他選擇的架構裡都是危險的——鄰居們可以向福利部打些小報吿。在大約那個時候(指着照片)魯柏在前廊上坐在一個成年男人的腿上,而鄰居適時的報吿了這件事——意思是可能涉及了性的墮落。
魯柏的母親知道如果她被證明在任何方面不稱母職,或無法給予孩子適當照顧的話,孩子可能會被帶走。事實上,在拍這張照片一年多以前,魯柏就被寄養在一個天主教家庭裡,在那兒,不合傳統的想法不會被容忍。他在那兒體驗到沒有彈性的教條被謹慎的應用在日常行為上,而他在其中試着適應並且集中他深深的神秘天性(見附錄一)。
他記得他母親對他的經常苛責,但卻幾乎忘了當他回家以後他自己對她的咒罵之憤慨反擊。他一頭鑽進了天主教的世界裡,以非常頑固的勤奮追求它,把它用做為一種傳統架構,在其中他可以容許他的神秘天性成長。
當那天性長到超出了那架構時,他便離開了它。所有那一度看來彷彿如此合法的信念於是乎被看作是一種阻礙,而所有其缺點都變得顯而易見。當他在追隨着那架構時,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令他脫離它,而在此(輕觸照片),在這個小孩子的照片裡,那不動搖的天性、那很大的自發性已在那兒,而在尋求一個可以容許它成長,卻又能給了他一種安全的幻覺的結構。
那看起來沉着的孩子在某些方面其獨斷不屈並不比魯柏差。但離開了教會架構之後,魯柏就緊抓着心智來對抗他的直覺。在這照片裡的孩子確信基督的雕像移動了,然而,沒有一個架構去容納那種經驗,這成長中的孩子只好將之壓抑下來。神秘經驗變得只可透過詩或書而被接受,在那兒它被接受為具創造性的,卻沒有真實到會給他麻煩,或顛覆了那個“新的”架構。新的架構把這種迷信的無稽丟在一邊,心智被控制住了,而藝術變成神秘經驗之可被接受的轉譯,而且是那個經驗與自己之間的一個緩衝。他這種作法有點因噎廢食了。
那神秘天性走入了地下,而以科幻小說的方式重現。再次的,在那孩子的社會與宗教背景裡,非傳統的精神或具體行為可能帶來處罰。有一陣子那孩子可以在教會內詮釋神秘經驗——但即使在那時,他也總是與教會的權威有所衝突。
(十點十九分。)不過,若無此種如此熱烈追隨教會信仰之經驗,他就不會瞭解人們對96此種信仰之需要,也就無法象他後來那樣的能觸及他們了。最初,他的質疑頭腦就在他開始檢查宗教的信仰裡得到了鍛鍊。當他在很久之後接觸到靈異經驗時,他很害怕它會導致一種新的教條,而下決心不去那樣用它。
他的“保守主義”——他與保守的觀念之強烈認同——被用為一個跳扳,使他由他知道其他人所在之處跳進新的區域。他抵抗靈魂學之教條就與他抵抗教會之教條一樣的猛烈。
可是,他由教會的架構跳人了另一個架構,在其中,在藝術性作品的掩護下,神秘主義被“二手的”體驗了。而後,《意念建構》(注四)完全的震破了那個架構。
(停頓。)因為種種我已經給了的有關你們之共同關係及你〔指我)自己的目的之理由,為了讓一個更新而合適的架構能自行形成,需要一些時間——在那架構裡,魯柏可以自由的在一個實際的結構裡追求神秘經驗:在其中,非傳統的思想可被容許自由的延續下去。他感覺,可以取代他藝術的架構,就如他的藝術取代了教會。在他感覺安全之前,他身體上的癥狀(注五)的確被用做為一種架構,在其中自發性至少到某種程度被容許了精神上與心靈上的自由。
休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