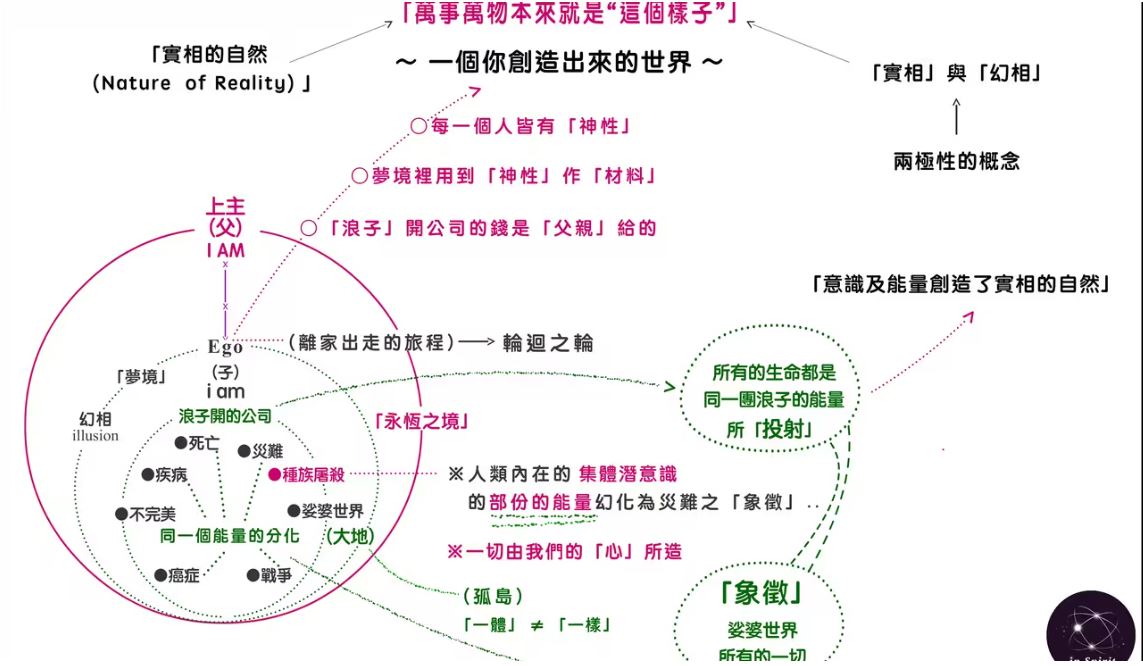赛斯-未知的实相一
夏日即冬日
今日即明日,而现在即过去,
万事皆空而事事皆恒久。
既无开始,也无结朿,
既无可堕落之深,也无可攀升之高。
只有这一刹那,这光之摇曳,
遍照空无,但哦!如此光明!
因我们即在太空颤动不定的火花,
燃尽永恒于一刹之恩宠。
因为今日即明日,而现在即过去。
万事皆空而事事皆恒久。
(罗的注:这是一九六三年四月,当珍二十三岁时写的一首诗的第二及最后一节。纵使在这不成熟的作品里,她的神秘天性已在肯定其与生俱有的知识。)
罗的前言
赛斯在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的第六七九节开始口授《“未知的”实相:赛斯书》,而在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的第七四四节完成。
赛斯如往常一样一节节的口授此书,但却取消了任何章节的形式。不过他的确把他的资料组合成六段,并且加上标题。如他在第七四三节里吿诉我们:“这本书没有章节,为的是更进一步的瓦解掉你们对一本书应该是怎么样的概念。不过,仍然有不同类的组织存在着,而且本书的任何一段都同时要求读者好几个层面的意识之参与。”赛斯并没有给每一节一个标题,因此在目录所列的每一节之后珍打算写上几句话,至少指出在那节里所论及的一些主题。
就像其他的赛斯书一样,《“未知的”实相》不只包涵了赛斯课,也还有珍和我对它们的想法,以及我们有关其制作环境的注记。
我很好奇想要知道,珍实际上花在制作这整本书上的时间大致有多少,经我计算的结果,她在九十点三五个小时的出神时间里完成了这本书,再加上休息时间总共是一百三十一点三96个小时。我觉得蛮迷惑的,为什么以前几乎每一个读者都忽略了珍制作赛斯书的速度,甚至珍本人对此也没有表示过多少好奇心。但我认为她的制作速度是对赛斯的概念——基本上一切都同时存在的一个最佳解释:时间并不存在,而赛斯书已经以完成了的形式等在那儿。
我认为偶尔在本书中提醒读者赛斯的某些基本概念是很重要的,举例来说,我会继续谈到时间——但却是赛斯的时间——的问题,把它和赛斯所说的一种“耐久性”(durability)一同来谈,这种耐久性同时是“自发性”及“同时性”的,如赛斯不只一次解释给我们听的。这个“耐久性”是透过“价值完成”之不断扩展而达成的。我在卷二的第七二四节之后的部分评论也适用于此:“如赛斯在一九**年一月八日的第十四节中相当幽默地说:‘……你们拫本不知道对一个必须花时间去了解的人解释时间有多么难。’然而,赛斯的‘同时性’时间并非绝对的,因为就如他在那节里也吿诉我们的:‘虽然我不受你们层面的时间所影响,我却受在我的层面上某些类似时间的东西所影响……对我而言,时间可以被操纵,可以悠闲的去用及检视。对我而言,你们的时间是一种工具,是我可以用来进入你们的觉察的几个途经之一。因此,它对我仍然是某一种的实相。否则的话,我就根本无法以任何方式利用它。’
我想,只要我们是具体的生物,就永远无法抓住赛斯“同时性时间”的观念,然而,它却对无形的机制提供了线索——我们就能比较了解珍眼中的赛斯。把概念变成文字这件事(尽珍所能做到的),有助于让我们抓住赛斯所讲的:我们可以对时间做出某种直觉性的、非语言性的触及或了悟,那多少超越了我们对所谓“时间”的素质或本质之陈腐概念,这陈腐概念在我们西方社会是如此的理所当然,以致于甚至去质疑其仿佛单方向的流动也是徒然的。
下面我要引用赛斯的两段话,然后再继之以珍的一段较长的话。
赛斯的第一段摘录是为了在两卷《“未知的”实相》之间创造一个桥梁,借由自其中一卷提出一些东西而将之放在另一卷里。再次的,由卷二的第七四三节:“没有一本名为《“未知的”实相》的书可以使得那个实相完全被认识。它仍然是星云似的浑吨,因为它在意识上并未被了悟。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指出那些比较看不见的区域,帮助你们探索你们自己意识的不同面……我十分明白这本书引起的问题比它回答的更多,而那原是我的意图……”
如我在某些注里引用的,珍早年的诗淸楚的反映出,她对某些赛斯日后详细阐释的观念之直觉性了解。就我看来,她对赛斯资料所负的任务就是提供这些基本上艺术性的概唸给我们有意识的运用,以使它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运用将我们个人与集体的实相变得更好;而我所谓的“艺术性的概念”是指人类所能表达并且争论的,最深、最美而且实际——并且,没错,神秘——的真理与问题。
在赛斯书里我们一直故意避免去评论存在于赛斯的观念及那些近东、中东或远东的种种96宗敎的、哲学的及神秘的理论之间的类似性。当然,这种方式适合我们的本性,珍和我知道此种关连性存在——的确,如果它们不存在我们才会觉得奇怪呢!别人常常跟我们谈到这一点,而我们也读了一些,好比说,谈佛教、印度教、禅与道家的东西,更别说像印第安巫术、巫毒及西印度群岛的巫术了。我们认为,显然可以写一本书来比较赛斯资料与其他的思想体系——不论它们是否是宗教性的,但因为珍和我都是个人主义者,所以选择了不去集中在那些区域。而我在此所说的也不是想要眨低其他对“基本的”实相之看法。
那麽,虽然在赛斯的哲学及许多其他有组织的思想系统之间是有相似处,但在我们看来也有重大的不同。珍和我倾向于认为,我们在我们世界里发现的那种一致性“涵括”了宗敎,而非被它们界定,而我们认为赛斯也强调此点。我们就这样顽固的向前走,明白我们的观点是根植于世界的西方传统里,但也知道在我们四周存在着许许多多其他的哲学或体系,它们之中有些已存在数世纪之久,那是人类创造出来解释实相的。然而,我们并不觉得我们非得深入了解,好比说,苏菲教或婆罗门教之细节不可。但我们不喜欢印度教与佛教的涅槃概念,它们主张通常在一连串的生命之后个人意识之灭绝,并溶入于一无上的神灵。而且我们反对那种说法:“大自然”以线性时间的方式做了这样的安排,使得个人必须在此生中对前生的行为偿还因果的债。如果大自然不处罚任何事,为什么要处罚任何人?涅槃和业报的实相并不是珍和我想要创造的。
反之,我们比较喜欢赛斯的——是我们自己的观念,关于个人意识之不可侵犯,不论在肉体存在之前、之中或之后,也不论是涉及了任何一种的转世理论。也许对我们这些活在西方的人而言,我们自然不会喜欢在肉体死亡时舍弃我们的个人性这种概念,即使在理性上我们能了解,比如说,佛教的教义说我们能在最终的、至乐的舍弃自身于一无上神灵里找到“完美的”喜悦——虽然我幽默的说,就我个人而言,我还不知道那个舍弃自己的人怎么知道他这样做了没有,如果他已被如此彻底的溶入了的话。
我比较同意赛斯在《灵魂永生》第二十二章第五九〇节里吿诉我们的:“你们不是命定要溶入于‘一切万有’。如你目前所了解的你人格的形貌将会被保留。‘一切万有’是个人性的创造者,而非毁灭它的手段。”而每当我读到传统东方对无上神灵的观念时,我就记起赛斯在《灵魂永生》附录里第五九六节说的:“在此,我用了‘意识的扩展’这个词,而非更常用的‘宇宙意识’,因为后者暗示了在此时人类尚不可得的那种比例之经验,与你们正常状态对比之下,强烈的意识扩展在本质上也许显得是宇宙性的,但它们仅只是对你们现在就可得到的意识之可能性的一个暗示而已,更别说能开始接近一个真正的宇宙性知觉了。”
我假定上面那四段话很显然可能引起许多非议,但在其中的资料很接近于珍和我在这些96日子里对赛斯资料与其他哲学之关连性的看法。我尤其觉得高兴的是,珍的工作及她对我们思想的贡献是出自她的心灵,而未得助于实验室、统计数字或测验。那就是说,我们对真正考验的想法是在观察,以看出赛斯资料能对实际的日常生活有何帮助。我们在一九六五到六六年做的,其他种类更“正式”的测验,详细的纪录在《灵界的讯息》第八章里;我们现在很容易忘记那些早期的测验是相当的成功,而且可以在任何时候再来一次。当我们在做那些测验时,我心里觉得奇怪为什么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当中,只有人类这种动物觉得有需要去建造实验室来“证实”他到底是什么,他的能力——心电感应、新陈代谢或其他——又到底是什么。这个题目本身就如此的庞大,以致于珍和我可以一直写个不完,因此,我只在这儿约略提及一下。
根据他认为他已知的东西,在他的实验里因此有很大的机会去获得预先设定的答案:他的外在化的设备几乎无法产生其他的结果。(一个科学家不称一个氧原子或任何一个其他元素为活的,更别说它们是具有意识的了。然而,某些原子聚合成的一个人形却称他自己是活的——而激烈的否定那些不幸存在于人类架构之外的一模一样的原子群同样的地位。)但在赛斯过去十年里所给的资料之中,他讨论过人们对一般人类状况之极度贫乏的了解的某些理由,而我也确信将来还会谈得更多。
我觉得极为欣慰,珍只用到她现有有形的身体及无形的心智就能持续地显示出人类不被认为具有的能力,我们不满意我们的社会——不论东方或西方——给我们的答案。对如生命的意义,其深度与神秘,其无穷尽的可能性这类问题,每个读者可以在赛斯的看法里找到他自己的意义。
以下是录自赛斯的第七五〇节,那是在他完成了卷二的两个月之后,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举行的,在其中他不只简略的说出制作《“未知的”实相》的动机,并且还论及他的一个我认为应该经常强调的基本概念,这一次还涉及了知觉。“《“未知的”实相》写来是要给……个人对实相的其他模式略见一瞥。它是要被用来作为一张地图,把人领入并非另一个客观的宇宙,而是进入意识的内在道路。这些内在道路或意识股(strands)带进来一些要素,使得人变得可能去了解,任何一个客观化的宇宙之内涵真的可以被十分不同地知觉到。你就是你所知觉的东西之一部分,当你改变你知觉的焦点时,你便自动地改变了客观的世界。并不只是当你知觉它为不同的东西时,它却还保持原状,而不论你的经验为何。知觉这个行为本身有助于形成被知觉之事,并且是其一部分。”
以下是珍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写下她作为赛斯的观感之摘录:
“当我是赛斯时,我只是他的实相之一小部分,也许只是我能捉住的那个部分,但96我却沐浴在那个人化的能量里。当赛斯把注意力转向人们,对他们说话或回答问题,那时我感觉到对他们的价值及个人性的一种几乎是多次元的欣赏。他了解每一个人的价值并向其致敬,以一种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人。我对赛斯对别人的反应的那种体验,使得我怀疑有一种比我们所知远较生动的情感经验存在。
“然而,我确知赛斯代表了另外一种朿西,一种不同的人性,而当那种样的生灵与我的主观世界相交时,赛斯就‘发生了’。
“在许多方面我们是一种孤独的种族。我们仿佛永远梭巡于我们自己的天性之藩篱内。也许我们对身份感的概念是有如我们绕着我们心智画的一个神奇的圈子,使得任何在外的东西显得是黑暗又陌异而‘非我’的。也许有远比我们自己亮得多的其他心灵之火照亮那内在的景观;还有意识的其他面,我们与之相连,就如我们与动物相连一样,在一种我们几乎不了解的存在之链里。
“我们爱‘向后’看我们的动物本源,我们设定所谓的进化已经结束,而我们在此欢呼——哈哈,我是万物之灵。但也许我们只是在中间,不完全的感觉到我们自己之其他遥远版本的存在,那将出现在一个远得我们无法理解的‘未来’。也许以那种说法,我是赛斯的某个远祖,活在我自己的生命里,却只是他生命里的一个记忆。但他坚持在过96去里也有新鲜的行动;所以如果事实是那样的话,我就仍在寻找我自己的途径。
“当我自己想到这么远的时候,一种奇特的加速攫住了我。我的身体变得非常松弛,但我的心智却有一种很奇怪的运动感,就好像我试图去了解的某些东西太快的掠过我,而令我无法追随;然而,我一直试着使自己旋转得更快些,以便追上去。如果我的一个细胞想要理解我自已的主观实相,它也许会有同样的感觉。我想我是活在赛斯的主观‘身体’内,就像我的一个细胞是活在我的肉体内一样。只不过,我一直在摸索……并且感觉那些我自己的实相并不能真的了解的事件。
“这也许只是当意识心试图瞥见它自己源头时的反应而已。也许当我们在做这种尝试时,象征性地说,就好比我们是暂栖在我们意识的平台上,同时向上也向下看。就像无重量的太空人,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却不太确定我们的位置,因为心理上它在内在空间里不断的改变。我们暂时的晕眩了,被一个自己与自己的其他版本所组成的内在宇宙弄得眼花撩乱,而感觉我们正旅游过某种庞大的心灵,它播种‘自己’就如太空播种星辰一样。”
最后,我们如何应付越来越多的读者来信呢?我们最近的作法是寄给读者三样东西,一封珍和我的短笺,一封赛斯在一九七五年四月里口授的信,及一张珍的书单。
96以前赛斯也会口授过一封信,读者可以在《个人实相的本质》第八章的第六三三节里找到。我们感觉赛斯这两封信反映出他资料的大半精髓,以及制作那些资料时我们的境况与心态。我们的确认为把赛斯的新信放在这里是一个结束这些注的理想方式(信中一如往常赛斯称珍为鲁柏,称我为约瑟)。
亲爱的读者:
鲁柏看过你的信了,约瑟也一样,我对其内容也是知道的。我们还没有任何外在的组织,因而没有秘书可以帮忙回信,也没有中间人去写花俏而预先包装好的回信。
鲁柏及约瑟是注重个人隐私的人。他们与宇宙也有种一对一的关系,这种特质是指他们抗拒形成任何组织,即使这种组织会有助于回信。所以我来口授这封信。虽然它会被寄给你们当中的许多人,但它却是写给你们每一个人的,而我只是觉得遗憾,我无法个别的深入于你们的热望、挑战与问题里。
你们有些人在喜悦中写信来,有些则在忧伤中写信来;你们有些人写信来诉说你们已找到的答案,而有些人则写信来要求答案。在任何情形里,能量都随著这封信送出去给你们了。
那能量会唤起你们自己的能力,它会引你们到只有自己能有的洞见与解决之道,它会让你们与自己存在的基础接触,而终究来说,所有的狂喜与答案都是由之涌现的。我的目的并非为你解决问题,却是令你与你自己的力量接触,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借由给你即使是最悲惨问题之“答案”而介入于你与你自己的自由之间。我的目的是要加强你自己的力量,因为终究来讲,你存在的神奇就足以帮助你找到成就、了解、丰富与平静。
你们的问题是被自己的怀疑所引起的,这些怀疑的升起是因为你们已与自己存在的价值失去了联系。让我在此加强那个价值,让我加强我对你们天生具有欢喜随缘而超脱任何你们现有问题之能力的信心。如果我迳自去替你们解决问题的话,那麽我就否定了你们自己的力量,而更进一步的加强了你们已有的无力感。不过,我知道你们可能会觉得累了,而有时候送你们一份能量可以令你们振奋一下,所以再说一次,随著这封信我送给你我对你的存在之欢喜的认可——以及你可以用来加强你自己的活力与力量的能量。
并非所有的信都是由邮差送达的,因此就你们所寄给我的信而言,你们每个人应该都有来自我的你们自己那种内在的回应。不过,我在许多方面是作为你们自己心灵的一96个发言人,所以那内在的讯息会是来自你自己更大的存在;由那个多次元的实相层面我向你致敬。
你和“未知的”实相(一)
赛斯序
(珍在出神状态中传述赛斯序的情况记录在第一部,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的第六八五节里,在那节的中场休息时,赛斯在十点五十七分开始讲下面的资料。)
现在:序:有一个“未知的”实相,我是其一部分,而你们也一样。
(停顿良久。)许久以前,我突然出现在你们的时空里,自那时起,我跟许多人谈过话,而这是我的第三本书,如果我是以一般的方式借由肉体诞生在你们世界里的话,这一切对任何人而言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反之,我却开始透过珍﹒罗伯兹说话,以表达我自己。在所有这一切当中都有一个目的,而那个目的的一部分就孕涵在现在这本书里。
每个个人都是未知的实相之一部分。可是,由于我的地位,我显然比大多数人更是其一部分,我在心理上的觉知联系了你们有意识地觉知的世界及其他至少仿佛逃过了你们注意的世界。我透过她说话的那个女人发现她处于一种不寻常的状况,因为没有任何理论——形上的、心理的或其他——可以适当的解释她的经验。所以这使得她去发展她自己的理论,而这本书是某些已在《意识的探险》(注一)里提过概念的一个延伸。为了写那本书,鲁柏汲取了能量的深源。
(十一点十一分。)可是,以你们的话来说,这未知的实相是未知到超过了最具弹性的意识所能企及的,而它只能被像我这样一个潜伏在其中的人格所趋近。不过,一旦被表达之后,它就能被理解。那麽,我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这未知的实相为你们有意识的知晓。
从历史上来看,人一度认为只有一个世界。现在他知道并非如此了,但他仍执著于一个神,一个自己,及藉以表达这自己的一个身体的这些概念。
只有一个神,但在祂之内有许多个神;只有一个自己,但在他之内有许多个自己。在一个时间里只有一个身体,但自己在其他的时间里有其他的身体。所有的“时间”都同时存在。
(停顿良久。)以历史性的说法,人类选择了某一条发展的路线。在其中,他的意识专门化了,集中焦点在极为特殊的经验上。但心理上及生理上来说,永远与生具有改变那个模式的可能性,一种会有效的把人类提升到另一种气候的改变。
(十一点二十二分。)不过,这样的一种发展首先需要宽广化对自己的概念,并且对人类潜能有更大的了解。人类意识现在正在一个阶段,在其间,这种发展不只是可行的,并且是必要的,如果人类想要达成他最大成就的话。
到某个程度,珍﹒罗伯兹的经验暗示了人类心灵的多次元本质,并且给予潜藏在每个个96人内的能力之线索。这些都是你们种族传承的一部分,它们显示出那连接你们居于其中的已知与“未知”的实相之心灵桥梁。
只要你们对自己的本质仍然持有非常侷限性的观念,你们就无法开始理解一个多次元的神性或一个宇宙性实相,在其中所有的意识都独特而不可侵犯,却又热衷于形成具有组织及意义的无穷尽之完形(gestalts)。
在我其他的书里,我用了许多已被接受的概唸作为跳板,来把读者带到其他的了解层面。在这儿我想说明的是,这本书将开创一个旅程,在其中可能看起来熟悉的东西已被远远的留在后面了。但是当我结束时,我希望你们会发现那已知的实相甚至变得更可贵、更“真实”,因为你会发现它被一个“未知的”实相之丰富组织内外彻照,并看见那“未知的”实相在日常生活最亲密的部分浮现出来。请等我们一会儿。(在十一点三十五分停顿。)个人地及群体地,你对个人性的观念限制了你,然而,你们的宗教、形上学、历史,甚或你们的科学都依你们对你是谁或是什么的概念而定。你们的心理学并没有解释你们自己的实相,它们无法涵盖你们的经验。你们的宗教并没能解释你们更大的实相,而你们的科学也让你们对你们居于其中的宇宙之本质同样的无知。
这些组织与学问是由个人所组成的,而每一个都被对他们自己的私人实相之侷限性概念所限制:所以,我们将以个人实相来开始,而且也永远会回到它上面。这本书里的这些概念是想要扩展每个读者的私人实相。它们也许看起来很神秘或复杂,但任何一个决心想了解自己及其更大世界之未知因素的本质的人,都有能力企及。
因此,这本书有一个私人性的开始。珍﹒罗伯兹的先生罗勃﹒柏兹对他母亲的死(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想要有更多的了解。在一节课里(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第六七九节)他拿出一些旧照片。现在:死后生活之描述通常与众所接受的一个自己(oneself)的老概念及个人性(personhood)的侷限性观念一致。不过,我却利用那个机会来开始这一本书。
(停顿良久。)当“自己”活在肉体中时,它是多次元的。它是灵性与心理性本体的胜利,不断由无数的可能实相中选择它自己清晰而坚定不移的焦点(非常热切的)。当你没认识此点时,你就会把所有老的误解投射到死后的生活上。你预期死者与生者没多少不同——如果你真相信来世的话——但也许更平静些、更明白些,并且,如果运气好的话,更睿智些。
(在十一点五十一分停顿——然后非常强调的说:)事实是,在人生里,你很巧妙却又完美地悬在实相之间,而在死后你也一样。于是,我利用那机会来解释罗的母亲在死后所能得的大幅度自由——但也解释在她生时就在的她实相的那些成分,那在意识上对她而言是关闭的——由于人类对心灵本质的观念之故。我偶尔评论那些属于柏兹家庭〔包括珍〕的照片,但任何读者都可以看看自己的老照片而问同样的问题,把在此地所说的应用到私人经验上。“未知的”实相——你是它的已知的同等物(再次更大声的)。那麽,认识你自己,当你变得熟悉这些概念时,你的意识会扩展。我自己则代表你的存在之那些已然了悟的部分。我的声音自你也在其中享有经验的心灵阶层升起,所以,倾听你自己的“知晓”吧。
(快活的:)序言结束。
(十二点〇一分。)
注一:事实上这个月初(一九七四年二月)珍开始她《意识的探险:层面心理学入门》之最后完稿。不过,她已把她在里面所谈所有主题之细节整理好了。
译 序
王季庆
《“未知的”实相》是赛斯书中最厚又最难译的一本,原书两卷共有八百页之多,实在令人望之却步!但若存而不译,赛斯系列不但不完整,而且也漏失了许多精义。所以,在一九九三年春节期间,我和许添盛便放了串鞭炮庆祝“开工”了。
这本书的好处在赛斯和罗的序中已可见一斑。我自己则源源为其对“可能性”之讨论所震撼!这种“可能性”弥漫于所有的时间、空间,也就是,当你出于自由意志而选择了某一条路线时,那未被选择的可能性则会在另一个实相里,由你可能的自己去经验。这个理论可以说是匪夷所思,若去追究其“暗示”,会令人头壳发胀,并且兴起“无常”之感!
但在我译的另一本书《超越量子》里,物理学却已印证这了这种“大千世界”的理论,证明赛斯所说“每一个可能性都会被实现”的确是“可能的”!
而我们当下的每一刹那,并非受限于线性时间的过去与未来,却是由我们最深的源头冒出来的,是憋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一个“可能”。所以这种“非命定”和“无常”,不但不应令你恐慌或茫然,反而提供了你把握“当下”的理由,并且鼓励随机的创造性,因为你的人生“当下”就可被你改变!
以下是特别发人深省的几段,愿先引在此以飨读者:
·在细胞内的意识知道它自己的不可摧毁性,只改变了形式……虽然细胞实质的死去,但其不可侵犯的本质却未被出卖,它只不过不再是物质性的。
·所有的生命都是合作性的,而所有的生命都知道它的存在是超越其形体的。
·人这种意识强烈的与身体认同是必要的,以便把焦点集中于具体的操纵。
·所有自然的东西都有“精灵”……它们的确有一个能量的实相,而它们帮助把能量转换成物质形式……你感觉到风及其效应,但你却无法看到风,风本身是看不见的。因而这些其他的力量也是看不见的。……它们并不比风更善或更恶……因为你们通常想像,如果某些东西是善的,那麽必然有一个相对的恶的力量,但并非如此……以更大的说法,这些力量是善的,它们是保护性的,它们滋养每一样活的东西。
·没有了解或训练,你就必须“失去”你自己的意识才能觉知“其他”意识。
·“你的蓝图”之资料被织入基因与染色体,但却与之“分开地”存在。
罗记录了珍传述此书的时间,才不到一百小时。但我粗略估计我口译的速度,平均一小时一页。也就是说,我和许添盛埋头努力了八百小时才竟全功!(当然,原书还需算上罗写注和附录等所花的时间。)无论如何,在一九九四年春节前,我们完成了此书,整整一年的苦功!希望读者耐心、细心的看完,也与我们一样,同感这是值得的!
特别要感谢陈建志费心校订此书,并提供宝贵的意见。
第一部:你和“未知的”实相
第六七九节 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 星期一 晚上九点四十一分
(在课开始之前,我给珍看一张她童年的照片,还有一张我的。这两张照片差不多同样尺寸,大约3.25×5寸,都相似的褪色易脆——好像是在同一个时候拍下来的——虽然我那张比珍的要老上二十年。
(我那张照片是我父亲拍的,并且记下了日期,已经在我们的家庭相簿里放了五十三年了。那张照片是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照的,那时我差不多快两岁,有一头卷曲的浅色头发,穿着小西装、白色长袜及黑皮鞋,站在位于宾州东北的一个叫曼斯菲尔的小大学城,我父母租的房子的边院里。大约有一打小鸡聚在我脚边的草地上,而我颇入迷的向下看着它们。在我身后有个焦点模糊、不知名的十来岁女孩,坐在由树干上悬下的秋千上,而在她旁边有一个空的藤编婴儿推车〔我的吗?〕,在她后面的私人车道上停有一部有蓬顶的四门汽车。曼斯菲尔离珍和我现在住的纽约州艾尔默拉城只有三十五哩。
(珍的照片已有三十三年之久了,那是由一位较年长的女士替她拍的,她招待珍到纽约州的度假圣地撒拉托加温泉市市外的一个温泉区去玩。那时珍与她卧病的母亲玛丽及一位帮96佣住在那个市里。珍把她朋友的名字及日期以幼稚的字迹写在照片背后。许多年之后她告诉我:“我妈妈恨那个女人。”在那张快照里,那是在一九四一年八月的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珍那时是十二岁,她坐在草地上,后面有一些长绿灌木,她用右手撑地身子略为后倾,两只光腿颇为一本正经的交叠。她穿着一件特洛伊市天主教孤儿院送她的印花布衣裳,那个孤儿院离她家有三十五英哩,在此之前她曾在那儿待过十八个月,那时她的母亲正在另一个城里住院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珍还穿着一件短袖套头毛衣,那是她母亲在住院时织的。
(珍的金发——后来变得颇黑了——整整齐齐的中分梳理,上头还夹着一个发夹。她有着一张年轻的圆脸,但却面无笑容,她并没皱眉,而只是直视着照相者,显出一种严肃而几乎不合她年龄的自制表情……
(对我而言,两张照片都有我觉得引人好奇的某种神秘感——一种气氛,我猜部分是由于他们是老旧的、私人的、且是如此的不可取代,但长久以来我都觉察到有些与之相连的其他感觉。珍在一九六三年尾开始传述赛斯资料,而很快的赛斯就开始发展他可能性的概念(注一)。从此有许多次,当我看着这些快照时,我会发现自己在臆测环绕着那两个小孩的可能实相。现在我告诉珍,我了解我们每个人选择了那些要使它具体化——或以我们的话来说“真实”——的行动路线。但自从那些照片拍下来之后,我们可能的自己踏上的所有其他路线又96是什么呢?到如今,那些照片是否真的描绘我们不成熟的身影,我们认为并且一直就是的珍和罗?或从我们的观点,它们显示了一个可能的珍,一个可能的罗——两个早已走上他们自己的旅程到其他的实相里去了?我不太清楚我想知道什么,也很难向珍表明我的意思。也许我只是想要赛斯以一种更个人的方式谈谈可能性〔后加的:在那时我完全没想到我的问题会引发一本新的赛斯书〕。
(珍在出神状态变为赛斯的外在迹象其本身就非常有趣,而我不想加以忽略;的确,我常常描述它们。不过,真令我着迷的是她在课中所表现的我所谓大大加强了的意识或能量——而我总是在她的传述表面之下感觉到一股甚至更有力的能量之流。当珍安静的坐在她的甘迺迪摇椅里等待赛斯过来时,我这样想着。几分钟后,她的右手伸向她的眼镜,当她把眼镜拿下来时,她的眼睛比平时黑亮得多:她已在出神状态了,赛斯已在那儿瞪着我了。)
现在:晚安。
(“赛斯晚安。”)
(身为赛斯,珍翻看了一下我放在我们之间咖啡桌上的照片。)
我现在要谈这两张照片——但如果你想要的话,你也可以有关于任何一张照片的资料。
(“好的。”)
再说一次,你们每个人选择你们自己的父母及环境。你在两天以前的笔记里谈到与艺术有关的预知,以那种说法,预知也适用于你的出生,你在事前在无意识层面上已十分觉知你会碰到的那些情况,你选择了它们,并且事先把它们投射进入时间的媒介里。
不过,那些情况虽然在一种方式里被“设定”了,但在另一种方式却是非常具可塑性的,因此,各式各样的可能事件能自它们流出。预知性地说,你对任何一个行为或路线之结果在无意识上都十分的觉察。当鲁柏(注二)这张照片被拍下时,他已开始变得觉察到那些会主宰他未来生活的他全盘兴趣之所在,虽然其特定路线尚未被选择。
这些兴趣之中有一些对鲁柏目前的经验提供了一些解释。那时宗教的背景就已在了。由于他的偏好与要求,在三年级之后他从一所公立学校转到天主教学校(注三),这件事是他母亲所不赞同的,他母亲觉得公立学校比较好,对人际关系也较有帮助。鲁柏在那个年龄就相当有主见了,他强迫他母亲答应他换学校。他制造出如此的纷扰,大哭大闹以致于他母亲不得不答应。他甚至在那时就已很顽固了。
他一直是极有想像力的,他母亲也是一样。他母亲有点反叛社会,与社会上“不体面”的分子在一起以炫耀她的美貌。在很久以后,鲁柏也与他环境里“不体面”的男人约会,但母亲或女儿都没有见到彼此的那个相似性。到那时,鲁柏的母亲要鲁柏有一个可尊敬的、最好还颇富有的丈夫,而无法了解他为什么选择那些不肯随俗的人。
鲁柏选择了一个贫穷的背景,就像他的母亲一样。那母亲也很聪明,但为逃避(她的环境)之故,选择了依靠她的美貌。鲁柏则试着用他的头脑。那些资料(多年来在一连串的私人课里)已给过了。
(“是的。”)
鲁柏则以非传统概念之更大的架构来表现他的不随流俗。在其背后,作为一个受福利部组织救济之下的孩子,纵容自己、小小的奢侈或太不随俗的行为在他选择的架构里都是危险的——邻居们可以向福利部打些小报吿。在大约那个时候(指着照片)鲁柏在前廊上坐在一个成年男人的腿上,而邻居适时的报吿了这件事——意思是可能涉及了性的堕落。
鲁柏的母亲知道如果她被证明在任何方面不称母职,或无法给予孩子适当照顾的话,孩子可能会被带走。事实上,在拍这张照片一年多以前,鲁柏就被寄养在一个天主教家庭里,在那儿,不合传统的想法不会被容忍。他在那儿体验到没有弹性的教条被谨慎的应用在日常行为上,而他在其中试着适应并且集中他深深的神秘天性(见附录一)。
他记得他母亲对他的经常苛责,但却几乎忘了当他回家以后他自己对她的咒骂之愤慨反击。他一头钻进了天主教的世界里,以非常顽固的勤奋追求它,把它用做为一种传统架构,在其中他可以容许他的神秘天性成长。
当那天性长到超出了那架构时,他便离开了它。所有那一度看来仿佛如此合法的信念于是乎被看作是一种阻碍,而所有其缺点都变得显而易见。当他在追随着那架构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令他脱离它,而在此(轻触照片),在这个小孩子的照片里,那不动摇的天性、那很大的自发性已在那儿,而在寻求一个可以容许它成长,却又能给了他一种安全的幻觉的结构。
那看起来沉着的孩子在某些方面其独断不屈并不比鲁柏差。但离开了教会架构之后,鲁柏就紧抓着心智来对抗他的直觉。在这照片里的孩子确信基督的雕像移动了,然而,没有一个架构去容纳那种经验,这成长中的孩子只好将之压抑下来。神秘经验变得只可透过诗或书而被接受,在那儿它被接受为具创造性的,却没有真实到会给他麻烦,或颠覆了那个“新的”架构。新的架构把这种迷信的无稽丢在一边,心智被控制住了,而艺术变成神秘经验之可被接受的转译,而且是那个经验与自己之间的一个缓冲。他这种作法有点因噎废食了。
那神秘天性走入了地下,而以科幻小说的方式重现。再次的,在那孩子的社会与宗教背景里,非传统的精神或具体行为可能带来处罚。有一阵子那孩子可以在教会内诠释神秘经验——但即使在那时,他也总是与教会的权威有所冲突。
(十点十九分。)不过,若无此种如此热烈追随教会信仰之经验,他就不会了解人们对96此种信仰之需要,也就无法象他后来那样的能触及他们了。最初,他的质疑头脑就在他开始检查宗教的信仰里得到了锻炼。当他在很久之后接触到灵异经验时,他很害怕它会导致一种新的教条,而下决心不去那样用它。
他的“保守主义”——他与保守的观念之强烈认同——被用为一个跳扳,使他由他知道其他人所在之处跳进新的区域。他抵抗灵魂学之教条就与他抵抗教会之教条一样的猛烈。
可是,他由教会的架构跳人了另一个架构,在其中,在艺术性作品的掩护下,神秘主义被“二手的”体验了。而后,《意念建构》(注四)完全的震破了那个架构。
(停顿。)因为种种我已经给了的有关你们之共同关系及你〔指我)自己的目的之理由,为了让一个更新而合适的架构能自行形成,需要一些时间——在那架构里,鲁柏可以自由的在一个实际的结构里追求神秘经验:在其中,非传统的思想可被容许自由的延续下去。他感觉,可以取代他艺术的架构,就如他的艺术取代了教会。在他感觉安全之前,他身体上的症状(注五)的确被用做为一种架构,在其中自发性至少到某种程度被容许了精神上与心灵上的自由。
休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