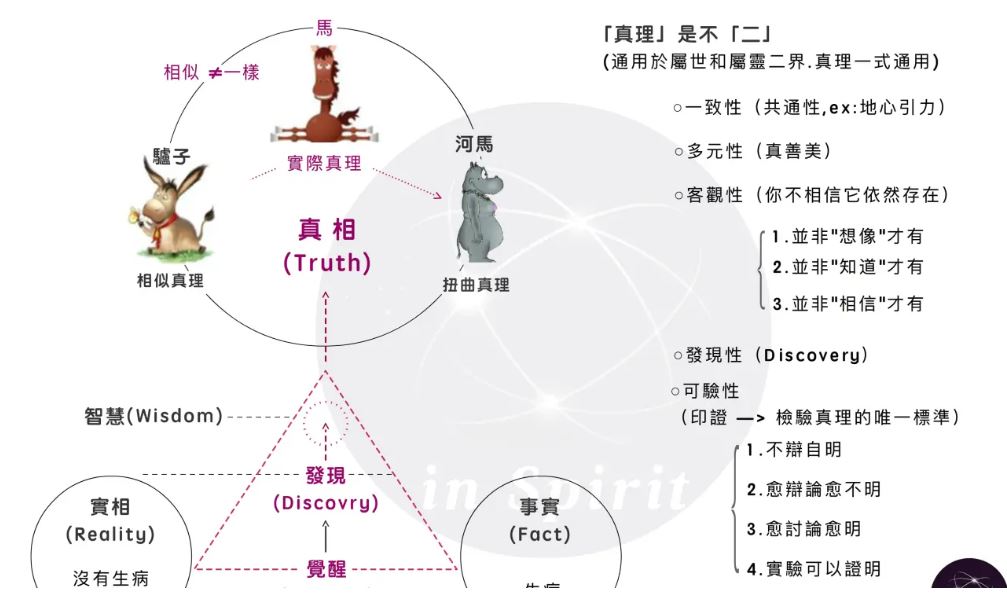(十点三十一分,珍不太记得她讲了什麽,但现在她的胃感觉到那资料在情感上的衝击——她告诉我,那是当资料具有一种私人的或“负荷着情感”的性质时,她常常会有的反应。)
(我提醒她说,我希望赛斯会谈到可能实相与她的旧照片之关连。)
(在十点四十二分以同样的方式继续。)
现在:你说对了,当然涉及了可能性。记得这一节的最先几句吗?一般整体性的情况被选择了,但关系到许多可能的路子。
(作为赛斯,珍指着她十二岁大的那张相片。)
那个孩子走了一条与这个女人(珍指着坐在摇椅裡的她自己)不同的路。那种独断性仍占优势。那孩子的神秘天性虽然很强,却没强到足以违抗教会的架构,强到足以离开它或超越它所提供的象徵。那个神秘
主义会被表达,却被削减了,心智会被覊束以使它不致问太多的问题。那个孩子(照片裡的)加入了一个修女会,在那儿她学会了按照可被接受的箴言去规范神秘经验——但无论如何,以相当规律的持续方式
表达它,在一种至少承认其存在的生活方式裡。
以你们的说法,与可能性的交会发生在那孩子与一位神父面谈的一天。那件事,以鲁柏的说法,及它在你们的可能性之内的结果,都在他《肥沃的苗圃》(RichBed)(注四)裡提及了。这个孩子在七或八年级
时写了一首诗,表达想做修女的愿望,而把它呈给了教区神父。在你们的可能性裡,那神父吿诉小孩她的母亲需要她;但他直觉性的看出鲁柏的神秘主义不会适合教会组织。
在另一个可能性裡,鲁柏在那时的愿望获胜了。他想办法把他的神秘主义的深度与广度稀释到足以让它
成为可被接受的程度。在那个另外的可能性裡,神秘经验并没有潜伏一长段时间,而也完全不需要把它变成新的方式。
写作能力被用来作为辅助的东西。在这个世界裡,艺术的能力被放在第一位,但神秘的天性则被给予了更大的机会去扩张与发展,而两者都被给予了去粉碎老的历史性架构,并且超越它们的机会与挑战。
(热切的:)在这儿的鲁柏选择了写作的架构,而坚守着它就如他一度坚守著教会一样的毫不动摇,但却又永远在寻找一个新的架构。有一阵子他把你理想化了,你的引导与力量成了他的架构。但当事情变得很明显,你也只是个人,而非一个架构时,他变得害怕了。当你鼓励他的神秘主义之浮现与表达时,那麽,他感觉你不再能做为一个可涵盖他的架构。到那时,他彷彿威胁到你们生活的共同结构。他直觉的知道你也用艺术的创作作为你自己与神秘的表现之间的一个缓衝。
为了所有我给过的理由——而它们是很清楚的交待过了(在私人课裡)——鲁柏很害怕不论精神上或肉体上的自发性会威胁到你们共同生活中久已被接受的架构。那麽,如果他在神秘经验裡自发性的前进,以他的想法,它会威胁到他的艺术被传统所接受。现在,那旧的架构所依之建立的对艺术与写作之传统概念不再适用了。
他感觉到,再一次的,他的自然经验把他领到超过了他认为安全的架构。
(十一点五分。)他还考虑到你,按照他的想法,他的这个经验不但用了他自己的时间,也会占用你绘画的时间。而在同时,那神秘的天性为其机会而雀跃,而感受到它自己的潜力。鲁柏下了决心放手去做(更大声)——同时,他也决定要保持旧的结构,而忽略在它裡面的裂缝。部分来说,他对你的忠贞以及他自认为他的责任是与使你专注于作为一个画家相连的,而不让任何事令你分心。然而,此时他就在令你分心了。
有那麽一会儿,你们共同的沟通系统摇摇欲坠。因此,他害怕放手去做。那些症状使他在家做他的工作,而且容许他集中精神不受外界干扰;让他继续写作,把神秘经验中规中矩的转译成艺术。
那些症状也被用来集中那絶妙的能量,同时,他也在思考该如何的去用它。他无法接受一个新的心灵架构,当在其中还有许多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关系到你们对事业的共同想法,以及各自对写作与绘画的忠诚.,还有你们一般而言对自发性之个人与共同的恐惧,以及保护你们的才能不受你们自己的性天性及别人干扰的需要。
他无法接受一个新的架构,而又不敢让旧的走。因此,那症状变成这些衝突之身体上的具体化,而满足了许多目的。这个孩子(在照片裡的),在她自己的可能性里长大,并没有遭遇到这种问题,那些挑战也不在那儿——只是以潜伏的形式存在。
请等我们一会儿……鲁柏非常需要明白你爱他,并且接受以你们的话说他现在的样子。
他由你那儿得到他所有能得到的那种作为人基本被接纳的感觉,那是你以你的方式早年从你的家庭裡所得到的。
约瑟,你的质疑及你对当今世界流行的理论之深深的不信任也强烈的为鲁柏所共享,而你们共同坚持要发现新的答案正引发了这些课以及将由它们而来的东西。
你见到他令人欢欣的潜力,而他也知道你知道。可是,作为一个情感丰富的人类,向着那个潜力摸索,他有时感觉失落,而需要被安慰。而如你现在所知的,去安慰他对你而言可能是蛮吓人的,因为这会使你们两人回到你在绘画裡所昇华的深沉情感上的觉悟及感受,甚至回到你也透过工作所接通的神秘经验。
休息一下。
(十一点二十五分,珍由一个很深的出神状态出来之后说:“我又有那种感觉了,你晓得,裡面空空的,就像赛斯说的话完全击中了要害……”
(自从上次休息以后,赛斯说的话我只删掉了二句非常个人的资料。显然的,珍和我的确选择了去面对十一年前她的心灵能力出现所带来的挑战。那些“新的”能力提供了如此明显的可能的创造性,就我们的本性而言,我们非这麽做不可;在我们的怀疑与质疑之下,我们直觉地感觉到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发现我能以某种方式做心灵性的贡献,而非只是记录这些课。而透过灵异的方法或任何其他方式能让至少有些我们最深的愿望及动机被带到如此清楚的意识上的觉察,这比我们在以前所认为可能的要多得多了。我们发现这种资料在较大的社会范围裡特别有价值,除了这些以外,我也很渴望得到有关绘画的哲学及技巧的任何可得的知识。
(我希望赛斯所给关于我自己家庭的资料会激发其他人的洞见。在十一点三十七分继续。)
让我们暂且短短的谈一下这个。
(赛斯—珍拿起了我的照片,那是在我快两岁时照的(注六)。)
那个孩子享受着很棒的活力与安全的感觉。你的家庭关系一直是很好的,你大半被爱与肯定环绕着。你的双亲很年轻,你母亲那时已生下两个漂亮的男孩;而她以她自己的方式,而且在她自己的架构裡,也是个完美主义者——你父亲从来没瞭解到她这点。
在表面上,这家庭是非常传统的,但在其下却是极难处理的。在这家中存在著一些教条,比如说,这母亲被期待养出完美的孩子,而且她,至少表面上,应屈从于男人。
于是,你的母亲觉得,在这婚姻裡,每个人都扮演了适当的角色,因为在她眼中你父亲有远大的前程,而她则给了他两个儿子。到了后来,她才觉得他没有做到他该做到的那部分,而你开始感觉到不安全了。她曾强迫她自己把她所有了不起的情感力量集中在他俩所瞭解的婚姻架构裡;但你的父亲不肯把他自
己的能力贯注在文化与经济的结构裡,如在那心照不宣的合同裡他曾同意去做的。
她曾强迫自己以传统的方式侷限她自己的世界——但照她的想法,他拒絶把他的精力用在他们两人都已接受的社会与财务的结构裡。
几年之后,你开始感觉鲁柏曾感觉到的:创造力有它自己的危险性,它会引你到被接受的社会结构之外,而一定得被限制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之外。
(捡起我的照片:)你弟弟林登不在这张照片上,但却相当活跃。你坚持要用你的能力,而多年来试着把它们用在商业的模式,在那儿,那些能力在金钱上或社会上以及你的自我形象上都可被接受,最后,你“长出”了那个结构之外。当你那样做时,你做了一个人工的分野,那就是好的艺术品不会卖钱——但虽然如此,你还是去画。
你和“未知的”实相(二)
就某种意义而言,你会使你的创造力成为实在的,而林登则否,他会把它安全的保持在一个“游戏”结构之内——并不必然是一般所谓的游戏,而却是一个他可以在其中灵巧的製造模型的结构。他从不把他的创造能力用在一个实际的世界裡,因此,在那个游戏的范围内,它们可以安全的在实际世界外面。
他所拥有的那些能力本来可以被用在如他所瞭解的社会裡,但却被如此的处理了。在这样子的一种结局裡,分裂产生了,因此那些能力被分散了,有些被导入学校,有些被导入绘图,而其他的则被导入了他的模型。那些创造性的属性被分开了,因此它们能被安全的处理,却又能得到某程度的表达,而没被完全否认。
你自己的个性则是比较直接的,意思是你维持着一个更切身的焦点。不过,在拍那张照片的时候,你父母正开始发现他们的问题了。你出生的第一年是一个当你父母都充满了期待的时候。林登感受到那个缺憾。他是有安全感的,但却从没有你那麽安全,因为那时你父母之间的分歧正开始显了出来。
林登现在用文字作为一个容纳创造力与沟通的架构,而非直接去表达他的创造力。你在这儿(在照片裡)是一个比较会四处漫游的孩子,因为你在身体上感觉比较安全。林登在那方面来说,远不如你的富于冒险性。
(就我个人对赛斯谈照片资料的诠释,珍的照片是关于一个会变成我所知的珍之可能自己的人,而我的则差不多可说是一个一直活在这个实相裡的我之早年版本……〕
注一:赛斯告诉我们所有的行动本质上最初都是精神性的,简而言之,可能的实相流自我们可能看见,却选择不去具体实现的众多行为——或事件。但我们任何的举动一旦被想到就一直十分有效,而且被可能的自己在其他的实相裡把它所有的变化都实现出来了。至少在有些这些世界之间可能有沟通,珍在试图接触她的几个可能自己时略有斩获,而计划将那些实验及其他她希望做的实验写下来。
可参照《灵魂永生》第十六章及《灵界的讯息》第十五章。
注二:赛斯几乎总是以珍男性本体的名字“鲁柏”来称呼她,因此称珍为“他”。综合赛斯在一九**
年一月二日第十二节裡有点滑稽的评论如下:“姑且不论所有你们的肉欲故事,性是一个心灵现象,只不过是你们称为男性及女性的某些特质。不过,那些特质是真实的,而且瀰漫于其他的层面,就像瀰漫了你们自己的层面一样,它们是相反却又互补,而且合而为一的。如我以前说过的,整个的存在体〔或全我〕即非男又非女,而我却又称某些存在体显然是男性的名字,如鲁柏及约瑟,我的意思只是说,在整个的素质裡,那个存在比较认同所谓男性的特徵而非女性的特徵。
注三:珍正在把她一生的众多而常是混乱的细节写在她的自传《从这个肥沃的苗圃》裡。
以下是《肥沃的苗圃》的一个非常简化之大纲:珍是德尔默罗伯兹与玛丽柏多的独生女,当她的父母在一九三一年离婚时,她是两岁大。于是年轻的玛丽带著珍回到她父母家,住在纽约市撒拉托加温泉市的一个贫穷社区租来的一间屋子裡。那时,玛丽开始得到早期的风湿性关节炎,但仍儘可能的找工作做。
终于,珍的外祖父约瑟柏多——珍与他享有一种很深的神秘认同——无法再多养两个人,因此这个家就必须仰赖公家的救济了。珍的外祖母在一九三六年死于车祸,次年她的外祖父搬出了那间房子,到那时,玛丽已行走不便了,因此福利部开始提供母女俩偶然的帮佣。所以,当珍在三年级结束之后换学校时,她是九岁。当珍和我在《“未知的”实相》裡提供个人资料时,我们总是心怀着好几个目的。我们不只想给与课本身有关的背景资料,而且也想对隐在亲近的长期关系之下非常複杂的情感与身体上的因素提供一瞥。我们认为赛斯对我们情况的评论能更有助于读者瞭解他自己的96信念、动机与愿望。
注四:珍写《物质宇宙是意念建构成的》之经验记录在《灵界的讯息》第一章裡。
注五:身为赛斯,珍在《个人实相》的第十一章第**五节裡给了几页絶佳谈她身体症状的资料。
我们花了几年功夫才瞭解,在珍的症状背后,隐着她想瞭解并且表达她自儿时起便感觉到的,在她之内那非常强的创造性能量之努力。然而,在她写作的自己与她神秘的自己之间的衝突——如赛斯在《个人实相》裡所解释的——只是她直觉性衝动想要表达创造力的一面而已:当珍成熟时,她领会到她还有其他必须应付的挑战。其中就包含了某些老的家庭关系之解决——而我说的还并不包括过去世或可能的自己之人生,而只是根植于现在这物质实相的重大问题之解决。关于珍的症状与有关的事我们已累积了许多未出版的资料。它的大部分常常也适用于其他人,而终究有一天她会写一本有关这整个主题的书。
同时,珍在处理她个人的挑战上已有长足的进步;现在她的工作主要包含了,溶解掉她放在如何运用她的伟大能量週遭的那套保护性、象徵性的身体信念。
注六:我的父母生了三个儿子,我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日出生,我大弟林登生在十三个月之后,而小弟李察比我小九岁。
虽然我们三兄弟的天性与兴趣相当的不同,但我们小时候却处得很好。我们都在塞尔——宝州东北的一个铁道城——念小学和高中。我父亲在一九二三年在那儿成家,开了一间汽车修护店,当林登和我自高中毕业离开塞尔,而开始各自半工半读地念大学及艺术学校时,这个家就开始分散了。然后我们三兄弟都服了相当长的兵役,过了许久我才瞭解,我们的离家对父母的影响有多深。
赛斯有时讨论到柏兹家庭的成员,包括某些他们转世的样貌。可是,在开始《“未知的”实相》六个月之前,他说了几句我从此一直将之运用在我们物质实相的生活上的话:“每个人选择他的父母,接受了就环境与遗传而言的一堆特性、心态与能力,以供他在未来的人生中提取。永远都有理由,而因此,每个父母对每个小孩代表了一个无法言喩的象徵,而常常,父母双方会代表了显著的对比与不同的可能性,因此,那孩子可以比较与对比不同的实相……你的两个弟弟也选择了那家庭的情况,你父母对他们而言代表了相反而且具个人性的象徵,因此,他们看你父母的角度与你不同。不要和你兄弟失去了联络。”
由此类推,我父母也在他们的每个小孩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的创造或版本。
第六八〇节
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 星期三 晚上九点二十一分
现在,当我谈到可能的自己时,当然我说的并不是人格结构的某些象徵部分或用可能性这个概念来作为一个比喻。
意识是由能量组成的,因此,能量所暗示的一切也都包含在意识裡。那麽,心灵可以被想作是能量之高度充电的“粒子”之聚合物,遵循着某些法则与属性,而其中有许多是你们根本不知道的。在其他的层面上,动力学的律则可适用于“自己”之能量来源。将一个“自己”想作是一个意识之能量完形的核心。那个核心按照其强度将会吸引来那个本体所能有的整个能量模式之某些团块。
以那种说法,那个本体在诞生时是由许多各种这样的“自己”所组成的,连带著它们的核心,而具体的人格有完全的自由从那库存裡汲取。鲁柏的神秘天性是那整个本体的一个如此强大的部分,以致于在他现在的实相裡,以及在所选择的可能实相裡——如我在讨论这照片时所提到的——那神秘的衝动与表现被给予了展现的机会。当一个心灵组合强化到某一个点时,与可能实相之交会就发生了,因此,做为一个“自己”的成就就达成了。
在那整个本体之内也许有,好比说,好几个初萌芽的“自己”,而围绕着其核心可以形成具体的人格。
在许多例子裡,一个主要人格被形成了,而那些初萌芽的自己被吸进它裡面,因此,它们的能力与兴趣变成从属的或大半保持为潜在的。它们是“痕迹自己”(traceselves)。
不过,在许多场合,这种潜在的自己会与“主要的人格”一样的高度充电。既然,就身体上来说,必须要维持某种人格的结构,所以就造出了“痕迹自己”。因此,当这种情形发生时,其他充电的自己之一或二个会真的跳离你们所知的时空结构。
从你们的观点来看,这些能量的分支变得不真实了,可是,它们的存在就跟你的存在一样的确定。就能量而言,这种自己的增殖是一个自然的原则。(对我:)你的“运动员自己”(见附录二)从没有被赋与像你的画画或写作的自己同样的那种力量,他变成从属的,却在那儿以备汲取,透过你的运动而得到快乐,而把他的活力加给了你“主要的”人格。
若是他透过你的环境、情况或你自己的意图被给予额外力量的话,那麽,若非你的艺术家自己会变得从属性或补充性的,就是,如果“能量自己”具有差不多同等强度的话,那麽他们中之一就会成了一个分支,被他自己想完成的需要推进到一个可能的实相裡去了。你懂了吗?
(“是的。”)
(九点四十四分。)请等我们一会儿……你的父母真的根本没有共享同样的实相,然而,这并不像你也许会以为的那麽不寻常。在一个位于他们各自的实相之间的地方,他们相遇,并且产生互动。并不是他们不同意彼此对事件的诠释,而是事件本身就是不同的。
核心可以改变,但它将永远是具肉体的存在向外辐射的那个中心。具体来说,意图或目的形成了那个中心,而不管就能量而言它的实相如何。
就能量而言,“意图”有稳定的力量,再说一次,自己有一个中心,而这个中心扮演着核心的角色。这在这个实相裡你的家庭生活当中,你父母的行为对彼此而言是不透明且看不懂的。有很强的能量换档,因此,两个人并没有直接相遇。请等我们一会儿……这些东西有些相当难解释。以某种方式来说,他们是没聚焦的,然而,每个都有很强的能力,但却分散了。这是有理由的。
在他们自己内包含着强烈却模糊的才能,那被孩子们用来做为能量的泉源。等一会儿……就他们共同的实相而言,他们的相聚完全是为了使这个家庭诞生,而没有其他主要的理由。那麽,他们播种了一代。
你母亲喜爱物质实相,而虽然她抱怨很多,但却在世界最微小的面貌裡得到最大的快乐。
你的父亲也爱物质实相,却从不信任它。这次,以你们的说法,你父母最强的实相是在一个可能的实相系统裡——而这儿(在这个实相),他们是分支。对他们而言,这个系统永远好像很奇怪似的。
在另外一个实相系统裡,你父亲曾是——事实上仍旧是——一个有名的发明家。他从未结婚,却把他的机械创造才能发挥到极致,同时,却逃避情感上的承诺。他遇见史黛拉(我母亲),而两人准备结婚——就年代而言,历史性的说,那是发生在同样的年代。那麽,在你父亲如你所认为的过去,他一度遇见了史黛拉,而他却,没有娶她。他的爱是对机器、摩托车的速度,把那个创造力和金属混合起来。在那个交叉点,在他之内相等的欲望及意图变得像两个双胞核心。发生了能量之全盘重组——心理与心灵内爆了(implosions),因此,两个同样有效的人格在一个世界裡变得觉察了,在其中,在一个时间裡只能有一个活着。
显然,那创造性的、有机械发明才能的人格开始超过了另一个。所以,你所知的父亲是那可能的自己。不过,那可能的自己在处理另一个所避开的情感实相,而这的确是他唯一的意图。
(在十点七分暂停。)这并不表示这样一个人格基本上是狭隘的,或他不在四周收集一些新的兴趣及挑战。因为他本身是活动的,他甚至有另一个自己的许多特性,虽然,这些自然是潜在的。但藉由生养小孩,你的父亲带来了具有实体而活生生的情感性存在——他的儿子们——之诞生。在他说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因为那发明家不够信任他自己去感觉太多的情感,更别说生出情感性的生灵了。在那个你父母最初相遇的另一个可能性裡,你母亲嫁给了一个医生,变成了一个护士而帮助
她丈夫行医。在一个女人要经过相当的努力才能站出来的时代——再次的,在你们的历史范畴裡——她变成了一位独立的妇人。
她生了一个儿子,然后故意的做了子宫切除术。她严格的教育自己,进入社交圈子裡,而藏起她自己未受教养的、天真的那些面。举例来说,在那一生裡,她显然不会在她的头髮上繫上红色的蝴蝶结。虽然她很成功,但所有这些被控制住的能量令她心裡多少有点苦。她死在五十九岁时——你听懂了吗?
〔“是的。”〕
不过,她的能量是那麽强以致于溢出到这个系统中和你父亲在一起的你母亲身上。有一天,我会就能量模式的说法试着把这点解释得更清楚。不过,历史性地说,许多可能性同时存在。当你的母亲在一个可能系统裡在五十几岁死去时,在这个系统的你母亲是那回去的能量之接受者。
你父亲之最大活力是在那发明家的实相裡,因此,以你们的话来说,你这个父亲就吃亏了。这并不是说
每个人格——不论在那个可能性——没被赋予自由意志及其他等等。在不论那个系统裡,每一个都是由一个源头完形能量生出而发展的。
所以,当你的照片被拍下时,你父母已经是活在一个可能的实相裡,但你及林登则否。
现在,休息一下。
(十点二十五分,珍的出神状态非常好。她说当她沉浸于其中时,她认为这资料“简直複杂透了……像
是‘在所有这些裡面,你在那裡——你的灵魂在那裡?’”
(我跟珍说,如果我母亲在她五十几岁时收到了任何额外能量的话,她也许会透过我们社会的习俗来表现其利益,也就是说,以改变而非可能性的说法,说:“当我做了那个决定时,我的人生从此就变得更好了。”我又说,也许,对我们现在而言,重要的是把赛斯有关更大的自己或全我的概念记在心裡,去观察我们正在绽放的生命,而因此获致我们可以以可能的说法来诠释的洞见。因此,我们决定不请赛斯回头去给我们我母亲之可能自己在她的实相裡的儿子之资料,即使那个儿子是我的一个可能自己。
(当我们在聊的时候,珍决定回到出神状态;她自己正得到有关那资料如此多的“渗漏”,以致于她开始觉得有意识地混乱了起来。但她说,如果她有时间去传述的话,赛斯已准备好所有的资料了。在十点四十五分继续。)
现在,基本上,自己没有侷限,而自己的所有部分全是相连的——因此,可能的自己们是无意识地觉察到他们的关系的。
因为没有系统是封闭的(注一),所以在它们之间有能量之交流与互动。这裡面有些是极难诉诸语言的,因为“结构”这个字本身不仅是系列式的,并且是粒子性的。
(暂停。)举例来说,你们把存在想作是粒子,而非想作有觉性及警觉的能量波,或想作是模式。(停了一分钟。)举例来说,想一下鲁柏在《意识的冒险》裡的生活环境。想像在十三岁时三个强大的能量中心来到了那人格的表面——高度充电的。因此,一个人无法充分地满足他面对的那些欲望或能力。因此,你可能在十三岁时有一个三角的分裂。在四十岁时这三个自己的每一个可能认识到十三岁为一个转折点,而奇怪如果他们选择了其他的路子,可能会发生什麽事。
这些全都不是预先决定的。一个分支的可能自己也许在好比说十三岁时离开了你的实相,但为了种种理由,可以在三十岁时与你再交会——而对你而言,你可能突然改变了职业,或变得觉察到一个你以为已忘掉了的才能,而发现你自己以惊人的轻而易举在发展它。
(再对我说:)你的出生与在那另一个实相裡你母亲孩子的出生同时发生,因此,她对你有强烈的感情。
你的出生及你小弟李察的出生对她而言是非常兴奋的——你的是因为刚才给的理由,而你小弟的则因为它代表了在那另一个实相裡你母亲的子宫切除的时间。在这个实相裡,李察的诞生代表了你父亲与情感的实相打交道的最后尝试。你父母双方都把他们天性之最强烈的情感特质灌输给第三个儿子。你的母亲在通常的生育年龄之后反叛地怀了他,这几乎是针对那〔可能的〕子宫切除术之反应。在这个世界裡,她可以并且要有另一个孩子。
林登是这婚姻唯一“自然的”孩子。小心你如何诠释这一点,但他是最没被另一个实相影响的孩子。不过,因为那个理由,而且因为你父母的个性,在心灵上就没有给他同等的注意力,而他也感受到那个缺憾。
(十一点二分)请等我们一会儿……我吿诉过你们,在一个可能性裡,鲁柏是个修女,在一个极度纪律化的范畴裡表达神秘主义,在那裡,那神秘主义必须被监视,因此它才不致于失控。因为在此有一个资料及经验之无意识的流动,因此,这成了在一些灵异的事上鲁柏的谨慎以及他害怕把人领入歧途的理由之一。有三个分支:一是那修女,她的神秘主义被传统地表达了,但却是在谨慎的环境下:一是作家,她
用艺术来遮掩神秘经验:还有一个你所知的鲁柏,他直接的体验神秘经验,也教别人这样做,而且藉由写作形成了两面之联姻。那麽,你已知这些自己之中的两个,而鲁柏在与《意念建构》一同诞生时,你也在场。
请等我们一会儿……约瑟的诞生是发生在约克海滨的跳舞事件(注二)时,因此,在你自己的经验裡,你的例子是发生在成人生活裡的。当然,我无法在一个晚上吿诉你所有的事。在我对鲁柏说些话之前,再给你几瞥好了。运动员很能赚钱,因此,为这个及其他的理由,你先前转向了商业艺术——那是个艺术才能会得到好代价的职业。
还有其他似乎琐碎却中肯的关连。你喜欢画室外场景的漫画:在运动中的动物,在表演中的身体。就如观众看一个运动员的表演,因此,那些看漫画的人观看你的演员在书页间表演动作。全是隐藏的模式,然而每个都有意义,我将会谈约瑟的出生,不过,现在给鲁柏几句话。
(十一点十五分。在给了珍两页的资料之后,赛斯在十一点三十三分结束此节)
注一:赛斯自这些课刚开始时(在一九六三年尾)就坚持没有封闭的系统——而在这样做时,就给了我们他自己至少能旅游过它们其中之一些的线索。
由一九**年一月二日的第十二节:“我比你们有更多可运用的感官,因为我不只觉察到我自己的层面(我明白在我能看那些其他层面之前,必须发生的改变将发生在我内,而非在那些层面内。”
或实相),也还觉察到你们的及其他的平行层面。“虽然,我自己并没有在有些其他的那些层麵裡存在过……”以及:“虽然我比你们对这些事有更大的瞭解。但还是有某些环境是我无法由我的视角看到的。
由一月六日的第十三节:“如果我以比喻及意象来说话,那是因为我必须与你们熟悉的世界发生关连。”由一月八日第十四节:“在你们层面上的每样东西,都是某些独立存在于你们层面之外的东西之具体化。”
由一月十三日第十五节:“想像力能容许你们进入这些层面……假装你不但瞭解你们猫的时间观唸到某个程度,并且还能透过那猫〔威立〕自己去体验它的时间感,在如此做时,你不会以任何方式干扰、抑制或激怒那猫。它也不会觉察到你的存在,而这也不能被当作是任何一种的侵犯。
“再进一步想像,纯粹做为一个观者,你实际的由内部体验到这样一件毛茸茸的外衣及所有其他猫的设备之感觉。这个可以大略代表我旅行到其他层面的一个比喻。由此推断,我无法旅游到比我自己“更高”的环境,在那儿,更鋭利的感官会即刻的知觉到我……在许多层面上,我们完全可被在那个层面上的人看见。对某些层面而言,我们是不可见的;而对我们而言,有些层面是不可见的。
“如我前面说过的,感官按照具体化的层面而改变。如果你说的是我现在的形象,我可以是许多形象。
那是说,在限度之内,我可以改变我的形象,但在如此做时,我并非实际改变了我的形状,而比较是选择变成某个东西的一部分。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初期的形象是一个人的形象,但它不是以与你们同样的方式具体化的,我可以选择随时把它非具体化。不过,以你们的话来说,它根本不是物质的,因此,此处我想我们会碰上〔你们瞭解的〕牆了…”
见《灵界的讯息》第三章所引之第十二节。
注二:见《灵界的讯息》第二章。
第六八一节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一日 星期一 晚上九点二十八分
(我们从九点十分起就开始坐等上课,珍在九点二十五分说:“我只是等着。我可以感觉赛斯就在身边,先前我就在得到一些东西,但我只是等着,直到它被完全准备好。我可以感觉观念在我脑子裡,但它们还没清楚,还没到它们应该是的样子。看起来赛斯要解释它们蛮困难的呢!”)
现在:晚安——
(赛斯晚安。)
——鲁柏说得不错,所以,请等我们一会儿……
我将要解释的东西的确很困难,我故意的还没把它放在任何的书裡,只因为在这些概念有任何被接受的机会之前,某些信念先要被去除掉。
以你们的话来说,其实,并不是我想保留什麽,而是,以下所说的必须依赖对先前所说观念的一个瞭解。我们必须帮助那些还在担心一个灵魂、神与魔的人们,去与比他们自己架构更大的实相建立一个瞭解,并且可能的话,温和的领他们离开他们自己的架构。我曾经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谈可能性,使得其他的实相披露出来,让这些人知道选择是可能的。
不过,更深的解释则要求对意识这概念更进一步的扩展,还要有某种的重新调整方向。极端重要的是,你们心裡要记住自由意志的重要性,以及如你们所认为的你们自己身份的在场。有了这个开场白,那就我继续吧!
附带一句,这并不是鲁柏词彙的问题,因为即使是一个专业的科学家也只会以其扭曲的方式提出这些概念。就你们所熟悉的语言而言,它其实是个基本的、语言本身的问题。举例来说,对我想传达的一些概念根本没有适当的字句存在。无论如何,我们开始吧!
所有可能的世界现在就存在,在任何一个实相裡,那最微细的方面之所有可能的变奏现在就存在。你经常不断的在可能性裡穿出穿入,一边走一边东挑西拣。在你身体裡面的细胞也在做同样的事。
(缓慢的:)我过去曾告诉过你们,有“活动”的脉动,在其中,你一明一暗的闪烁——这用于即使是原子或次原子的粒子(注一)。你只把是“你”信号的那个活动指认为真实的——现在就在场的那个。“
你”并不觉察到其他的活动。当人们以一个自己的观点来想,他们当然只与一个身体认同。你们知道身体的细胞结构不断在改变,不过,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的身体是由那丰富的可能性活动之库藏裡形成的一个能量之大块聚合物。身体并不像平常所想的那麽稳定。在更深的生物性层面上,细胞横跨种种可能性,而触发反应。意识骑在刚才提及的脉动之上,并且在其内,而形成它自己身份的组织。可是,每个可能性——只有由另一个可能性的观点或与其关系上,它才是可能的——都是不可侵犯的,因为它是不可被毁灭的。一旦形成了,那模式将追随它自己的天性。
(在九点五十分停了一分钟,头低着,眼睛闭着。)就像细胞长成器官一样,意识的组织也会“长”。那麽,一群可能自己可以,并且的确会形成它们自己的本体结构,而这个结构对所参与的可能自己是颇为觉察的。在你们的实相裡,经验是依赖时间的,但并非所有的经验都是如此被结构的,举例来说,有些平行的时间也被很容易的跟随,就像你跟随有顺序的事件一样。
可能性结构处理在所有层面上的平行经验。你的意识挑来选去,而只接受某种全盘的目的、欲望或意图之结果或分支为真实的。你透过一个时间架构追随这些。你的焦点容许其他也同样合法的经验变得看不见或没被感觉到。
以同样的方式,你执着于一个个人生物上的历史,你也只执着于一个整体的地球历史。所有其他的一直在你周围继续着,而其他你自己的可能自己们经验着与你历史平行的他们的“历史”,就感官资料的实际说法而言,那些世界并不相遇,然而,以更深的说法来说,它们是重合的。可能对你及鲁柏发生的任何无穷无尽事件之任何一个都发生了。只不过你们注意力的长度根本不包括此种活动罢了。
(十点。)这种无尽的创造力看起来可以是如此的令你目眩神移,以致于个人会像是失落在其中(注二),但意识在所有的层面形成它自己的组织及心灵上的互动。任何意识都自动的试图在所有可能的方向表达它自己,而且的确也这麽做了。在如此做时,它会经由它自己的存在体验到“一切万有”,这当然是经过它自己那熟悉的实相诠释过的。你长出可能的自己就像一朵花长出花瓣一样。不过,每个可能的自己将会在它自己的实相裡走到底——那就是说,它会去经验它天生具有的那些幅度到它最完全的地步。以你们的话来说,你们挑选出一个出生及一个死亡。
(对我:)可是,在你所认为的这一生裡,作为一个年轻的男孩,你死于一次手术裡了你又在战争中阵亡了,那是在你当飞行员的时候——但那些却并非你官方性的死亡,所以你并没认出它们。
科学喜欢认为它在与可预测的行动打交道。不过,它知觉如此小量的资料,而且在如此狭窄的一个范围裡,以致于任何分子、原子或波之伟大的内在不可预测性并不明显。科学家只觉知到那些出现在你们系统之内的现象,而那个常常看起来是可预测的。
请等我们一会儿……真正的秩序与组织——即使是有关生物性的结构——只能藉由承认一个基本的不可预测性才能被达成。我知道这听起来非常的令人震惊。不过,基本上,任何的波或粒子或存在体的动作都是不可预测的——无拘无束,而且未决定的。你的人生结构是那不可预测性的一个结果,你们的心理结构也一样。可是,因为你看到的是一个相当一致的画面,在其中,某些定律好像适用,你就认为那些定律先存在,而物质实相才随之而来。其实,那一致的画面是所有能量之不可预测的天性之结果,而那个天性是,而且必然是所有能量之基本天性。
统计学提供一个人工的、事先预定的架构,然后,在其中,你们的实相再被检查。数学是一种理论性的,有组织的结构,其本身就强加给你们你们的秩序与可预测性的概念。统计上来说,一个原子的位置可以被理论化,但没有人知道任何既定原子在任何既定时间位于何处(注三)。
(十点二十二分。)你们是在检查可能的原子。你们是由可能的原子所组成的。(停了一分钟。)请等我们一会儿……(停了一分钟。)意识若要完全自由的话,必得被赋予不可预测性。“一切万有”必须经常藉由自由地给它自己自由来令他自己、它自己、她自己惊奇。那麽,这基本的不可预测性就贯彻于所有的意识与存在层面上。一种特定的细胞结构在其自己的参考架构内也许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只因为相反的或矛盾的可能性没有在其中出现。
你和“未知的”实相(三)
以你们的话来说,意识是藉由接受,好比说,一个可能性、一个具体的生命,而终其一生维持其身份,而能维持住它自己的身份感(sense of identity)。即使如此,有些事件会被记住,而其他的则被忘掉。意识当它“成熟”时,也会学着处理替代的片刻(alternatemoments)。当它成熟到这个地步时,它形成了一个新的、更大的身份架构,就像在另一个层面上细胞形成为一个器官一样。
以你们的话来说——这句话是必要的——片刻点(the moment point)(注四〕、当下这一刻,是所有的存在与实相之间的交会点,所有的可能性流过它,虽然你们的一个片刻点可以被体验为你为其一部分的其他可能实相裡的几世纪或一次呼吸。
(在十点三十六分停顿。)鲁柏在这一刻感觉巨大(见附录三),他正体验到几件事。那内在的细胞身体意识觉得它自己很巨大,虽然对你们而言,细胞是微小的。举例而言,这个包装纸的声音(身为赛斯,珍捏紧了一个空的香烟盒包装),或指甲划过桌子(作出示范)的声音被放大了,因为在细胞世界裡,它们是一种重要的自身之外的宇宙性事件——具有很大重要性的讯息。细胞意识体验它自己为永恒的,虽然对你们而言细胞只有一个短暂的生命。但那些细胞是觉察到身体的历史的,以你们的话来说,而且是以一种比你们对地球历史的觉察更要熟悉得多的方式。当细胞在操纵身体过去与未来历史的时候,它们也以比你更熟悉的方式觉察到可能性。再一次的,鲁柏正体验到巨大感,在你们的可能性概念裡,细胞结构感觉其庞大的持久性。当它在处理一些对你们而言
甚至是不真实的事件时,它产生了一个实质的结构,那结构自一个庞大的创造性网络裡维持住身份感与可预测性。那个网络是不可预测的,但是由它鲁柏却能可预测的把烟灰弹到那个贝壳裡。(珍拿起她最偏爱的烟厌缸——那是由我们在一九五八年在下加里福尼亚半岛找到的鲍鱼殻做成的——而弹了一些烟灰进去。)那个姿势之可预测性是建立在一个不可预测性上,在其间,许许多多其他的行动可以发生,而在其他的实相裡也真的发生了。
(十点四十六分。)你最好给我们片刻,也好休息一下你的手。
(虽然有许多停顿,但珍已经在出神状态中稳定的讲了七十八分钟。现在她仍笔直的坐在她的椅子裡,小口的饮着啤酒。一分钟过去了。)
现在,你的信念与意图使得你由一群不可预测的行动裡选择那些你想要它发生的。你经验那些事件。(对我:) “你的”想活下去的欲望跨越了手术中那孩子的死亡,而那孩子想死的愿望选择了那个事件。人们就如原子一样的自由。请等我们一会儿,你完全无法预言你自己照片裡(注五)的那孩子会发生什麽,而你也无法“预吿”你现在会发生的事。你可以选择将任何数目的不可预测的事件接受为你的实相。在那方面来说,选择是你的,但所有你不接受的事件终究会发生。
以一种非常小的方式,当你想到你在暮年的母亲,而比较你与你的弟弟们对她的想法时,你可以看出这是怎麽运作的。她对你们每一个而言是一个不同的人。她是她自己,但在可能性的交织裡,虽然某些协
议过的历史事件被接受了,她却把她选择的你们的可能实相之不论什麽部分收进她的实相裡。你们每个兄弟都有一个不同的母亲。
那麽,可能性在你们的经验裡交会,而它们的交会你们就称为实相。生物上及心灵上,这些是交叉口、
交会点(coming together),是意识採取的一个焦点。
再次的,鲁柏仍在经验巨大感……所有那些自你出生就组成你的身体,并且一直组成它直到你死的原子与分子,以你们的话来说,现在就存在;因此,即使是你们对身体的知识也是在一个时间形式裡——也就是说一点一滴的——被经验的。
(在十一点五分停顿良久。)鲁柏的巨大感部分来自同时存在的身体之巨大感受。因此,对他而言,觉得身体大些。无法描述的计算发生了,因此,由这个基本的不可预测性,你体验到那些彷彿是可以预测的事。这只是因为你贯注于那些在你们实相裡“合理的”行动,而忽略了所有其他的。当然,当我说你身为少年而死去时,我并不是象徵性地说。而那垂死的孩子也没有把任何残酷的事实强加在那母亲身上,因为你母亲的那个部分就是后悔有了孩子的那部分。
现在:在同一时候原子可以以比一个还多的方向移动。你只科学地知觉到你有兴趣的可能移动。这同样适用于主观经验。
你可以休息一下。
(十一点十分。珍慢慢的由她最长的出神状态裡出来了,她在那状态下有一小时又四十二分之久。我只指出她许多长长的停顿之一些而已。
(她仍觉得巨大。她双眼上翻,然后又闭上:“事情真是怪透了,好像天空在裂开……赛斯谈到它好像是在控制下的事情,但现在我的头变得真的好大……”我把她叫醒,她说:“啊!真是怪极了……我不知道我应该把这种现象停下来还是继绩跟着下去,我觉得我的头现在真的好大,而且转向了右边,并且在打转——它大极了? ……”
(十一点十五分。“而当外界并没有任何声音的时候,每件东西都在营营作响——就像你耳鸣的样子,只不过更厉害些……现在,我整个的身体真的好大、沉甸甸的。我可能会结束它。那是很怪的:并不令人愉快。我的牙齿好像真的很巨大——每件东西——我的脚……”
(十一点十七分。当我再叫她时,珍微笑了:“我刚才有一个影像,我是在一个巨大房间裡的巨人,然后有些我不瞭解的事:一个我自己身为大猩猩或类似的什麽东西的影像。我跟天花板一样高,试想把牆打塌掉……我并不很瞭解到底发生了什麽。现在,我变得更大了。我想,我要出来了……我的脸没在干
什麽吧?有没有任何改变?”
(十一点二十一分。“我有种感觉,我的头髮很长而中分,就好像我有某种人类的五官;头髮从我脸的两边垂下,而我的脸有点像个动物,但有着非常聪明,且非常温暖柔和的眼睛。”珍终于睁开了她的眼睛。她仍然有耳鸣,声音那麽大以致于她问我有没有听到同样的声音。我告诉她我没有。我们绕着房间走,然后我做了半个三明治给她,她说:“有点令我戚到挫败,就像是我看到或感觉到在那一刻我能做到的,但我知道在那背后还有更多的,我能感觉到它,但无法把它弄出来。”
(她边吃边说:“在我嘴裡的声音真是响,那是一种我不时,她觉得那冰冷的液体流下她身体裡,却被错放在她食道的右边。她说出一串在她自己身体裡彼此相反的感受,那是她同时在她“更大的身体”裡也觉察到的:她的右脚非常冷.她的背非常热……我给了她一件毛衣,因为我们的客廒已凉了下来。二月的夜晚非常的冷。
(终于在十一点四十七分继续。)现在,只有由不可预测性才可能升起一个无限数目的秩序或有秩序的系统。
任何少于完全的不可预测性之事,最终都会导致停滞或在最后必会自我毁灭的存在秩序。唯有从不可预测性才可以冒出任何系统,那在其自己内是可以预测的。只有在移动的完全自由裡,任何“有规律的”移动才真正的可能。
从你们的梦之“混乱的”苗床,你有秩序的日常有组织的行动跳了出来。在你们的实相裡,你意识的行为和你分子的行为是非常相连的,你们这种意识预设了一个分子意识,而你们这种意识在分子意识裡是与生俱来的——在你们的系统裡与生俱来,但却非基本上可预测的。可预测性即意谓“着深具意义”。
不可预测性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看它自己,发现它自己的某些部分深具意义,而在它自己四周形成某些秩序或有秩序的顺序。在我们一节非常早的课裡,我吿诉过你们,你们由一个广大的范围裡,只知觉那些你们觉得有意义的某些资料,那资料只可能升自不可预测性的苗床。唯有不可预测性才能提供可能的秩序之最大来源。
一个细胞颇有能力处理不同种类的事件:因此,在梦境裡它们以它们个别的方式能知觉你的经验,而由之选择你想使之成真——以你们的说法——的那些事实。
在梦裡,你知悉可能事件,而后你从中选择;(对我:)所以,当你作为一个孩子而死了之前,你知道你可以选择那死亡。广义说来,你选择生与死二者,而你那张十六岁时的照片在那个实相里根本没有拍。
(停顿。)今晚鲁柏只能作这麽多了,而这只是一个开头呢。
(现在赛斯又来给了珍半页的资料,然后以这个开玩笑的话结束今晚的工作:)
他可能的脑子在一个时间只能翻译这麽多东西。
(“是的,晚安。”十二点六分,珍仍然觉得有些巨大。第二天加的几句话:她睡得不安稳,而发现她
自己“差不多整晚都在给谈可能性的资料。”她常常醒过来,而在这种时候,发现她没在讲一堂我没记录的课时,鬆了一口气。她笑着说,这样的话,那资料仍旧是“安全的”——我们在一节正规的课裡还会再得到它。
(珍常常告诉我,通常在这种场合,她并不觉得赛斯在场或听见他的声音。反之,她只觉察到那资料“跑过她”。)
注一:见《灵魂永生》第十六章第五六七节。
注二:早在这之前,赛斯就担心一旦我们试图抓住如他解释给我们听的,意识无尽的分支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渺小。如他在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第二十九节裡说的:“以后我会试着给你们看界限
在那裡——虽然(笑了一下)真的并没有界限,那些界限把各种层面〔实相〕形成一个关系圏子,在其中,因果关系多少如你们瞭解的样子运作。在那以后,将有很久的时间我都不需要再讲得更深。我会讲到存在体、人格、转世及不同的人格片段体集团,你们所熟悉或能瞭解的那些层面,而最后试着处理你们不管问了没有的问题:关于到底存在体开始是从那裡来的?”
“……不用说,我要你们瞭解还有比甚至这些还更多的,真正令人吃惊的複杂性,以一种我假定你会称之为‘完形’的方式运作的智慧,具有真正不可置信成熟度、觉性及理解力的活力‘构成要素’(building blocks)。这些是接近〔我所瞭解的〕终极的东西。“
这个资料不应令你们觉得自己不重要或渺小。这个架构是如此织就的,因此,每个〔意识的〕粒子是依赖每一个其他粒子的。其一的力量增加了全部的力量,其一的软弱削弱了全体,其一的能量重新创造了全体,其一的奋斗增加了所有每件东西的潜力,而这在每个意识上放上了很大的责任。
“我甚至会建议你们将上面那句话重複咀嚼,因为它是一个关键,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存在的每一面,面对挑战都是个‘存在’的基础。面对挑战是所有能力的发展者,而不怕用一个陈腐的说法,甚至最微小的意识粒子也有责任去用它自己的能力,而且是用它能力,到其极致。一切存在之物的力量及连贯性都依赖这自我完成的程度。”
又见《灵界的讯息》附录裡的第四五三节。
注三:我认为赛斯在他最后那句话裡,待别是与一九二七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所提的测不准原理(principle of uncertainty)或未决定(indeterminacy)原理有关。在量子力学裡这个原理是说,想要同时确定像一个电子这种次原子的“波—粒子”的动量及位置是不可能的。在这一课之后的次日,我问珍她有没有听过海森堡,她说没有,而在我儘可能的解释给她听之后,她也不瞭解。
注四:见《灵魂永生》第二章第五一四节及《个人实相的本质》第十九章第六六八节。
注五:既然赛斯由这张照片提到预言,这是一个好机会来看看他在较早的课裡所谈到关于他自己的预言能力,以及对这个题目的泛论。珍和我发现这是很有用的资料。
从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六日第二三四节:
“现在,常常预知性的资料会显得像是错的。在有些情形,这是因为一个自己选择了一个〔与所预言的那个〕不同的可能事件来具体实现。我可以通达可能性之‘场’,而你们不能……对我而言,你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彙整合一个。
“在另一方面来说,如我吿诉过你们的,你们持续地改变你们的过去。在你看起来它并没改变,因为你与它一同改变了……你以同样的方式改变你的未来,在这种情形,感知到可能事件的正确频道是必要的——正确是说最后将会被〔这个人〕选择〔来实现〕的那个频道。
“可是,这些选择是建立在你们对过去与现在之改变中的看法上。因为我比你们有一个更大的知觉范围,我就比较能预言将发生什麽。但这是依赖我对你们将做的选择之预言,而选择仍然是你们自己的……
选择之本身并没有与自由意志的理论相衝突,虽然自由意志所依赖的要比任何一个单独自我的自由要多得多了。如果自我被容许做所有的抉择,而自己的其他层面没有任何否决权的话,你们真的全都会在一种悲惨的处境了。
“因此,我对你们的未来可以比你们知觉得多得多,不过,我离全能还远得很呢。严格的说,这种全能也是不可能的。”
注六:非常简化地说:在现代物理裡是说,原子是过程,而非东西:原子或其组成物可以显现为波或粒子,要看我们怎麽观察它们;而这些特质存在于我们粗糙的时空世界之外。原子是可能性之模式。而又进一步说,我们描述或摹想此种非具体的品质之意图就不可避免的使我们误解了它们。